西贝风波一月后,预制菜仍是中国餐饮业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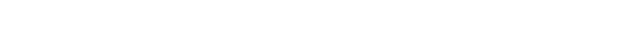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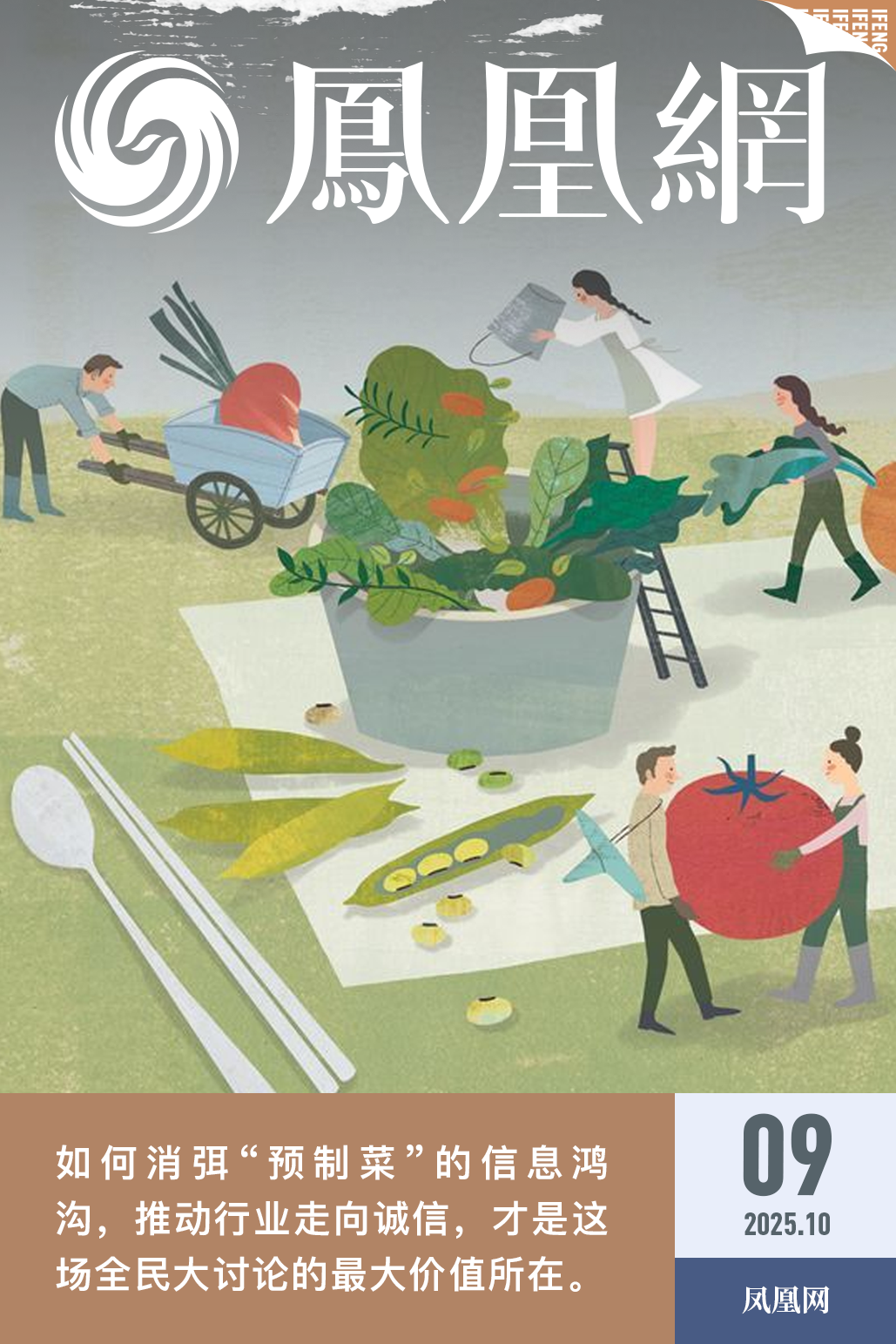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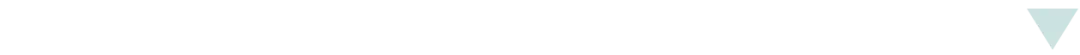
距离大V罗永浩在微博上点燃这场全民参与的“预制菜大讨论”已经过去一个月,在刚刚结束的国庆黄金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西贝XIBEI门店,已恢复了些许人流。
这一个月间,这家曾计划在2026年上市的餐饮巨头被贴上“贵价预制菜”的标签,一度门可罗雀,不得不频频出招。起初,西贝餐饮以官方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温情推文,讲述了“7岁的毛毛”以为再也吃不到西贝了,急得抱着店长大腿哭起来。被网友群嘲“史诗级拉垮”后,西贝将文章删除。最终,到了下旬,西贝靠“大放血”掰回一局:于9月24日广泛开撒100元无门槛堂食优惠券后,一些门店回归了排队就餐的局面。
据北京的消费者柳业观察,假期前一天,傍晚六点半,他和两个朋友来到北京海淀的一家西贝门店就餐,竟然在门口等位十多分钟——西贝陷入预制菜风波后,他去过两次,上一次就餐时,店内几乎没人——这天,他们点了9道菜,消费420元,用完两张代金券后,只付了220元。
有网友为此专门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到西贝领代金券“薅羊毛”的攻略,说原计账单223元、实付了17元,称之为“免费的晚餐”。
假期一结束,西贝再次加码撒券:10月9日起,消费实付每满50元送1张50元代金券。
一切都是为了自救。此前,西贝全国门店已开始“通货紧缩”,对菜品进行降价:草原嫩烤羊排原价 119元,现价109元;葱香烤鱼原价 89 元,现价 79 元;黄米凉糕原价29元,现价26元……
柳业倒是觉得西贝降价后的价格符合他对“下馆子”的预期,但仍有不少用户对西贝后厨揭示的“真相”耿耿于怀,说这是“年底预制菜清库存”。毫无疑问,西贝事件把公众又一次卷入食品安全的忧患中,但这场争论还远未结束。
全民唇枪舌剑中,最基本的概念一直很模糊:当我们在讨论预制菜时,“预制菜”到底是什么?事先准备的净菜是预制菜吗?冷冻半成品是预制菜吗?还是只有即食即热型菜品才叫预制菜?
凤凰网检索了微博上2000条有关“预制菜”的信息,发现消费者和从业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视角:
在消费者心里,预制菜和“保质期”长(出现162次)、没“锅气”(出现92次)、有“添加剂”(出现83次)联系在一起,它意味着我们可能失去食品安全保障和享用美味的基本权利;
而餐饮从业者最关心的“成本”一词出现了240次。预制菜的前途,关乎企业能否在九死一生的餐饮行业里存续。
食品安全博士兼科普作者云无心认为,“预制菜”是一个失败的术语。不但消费者和从业者自说自话,就连中国烹饪协会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预制菜”的定义都在相互打架。基于这个概念造成的混乱,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认知分歧已经形成。
因此他表示:如何消弭有关“预制菜”的信息鸿沟,推动行业走向透明、诚信和高品质,这或许才是这场全民大讨论,最有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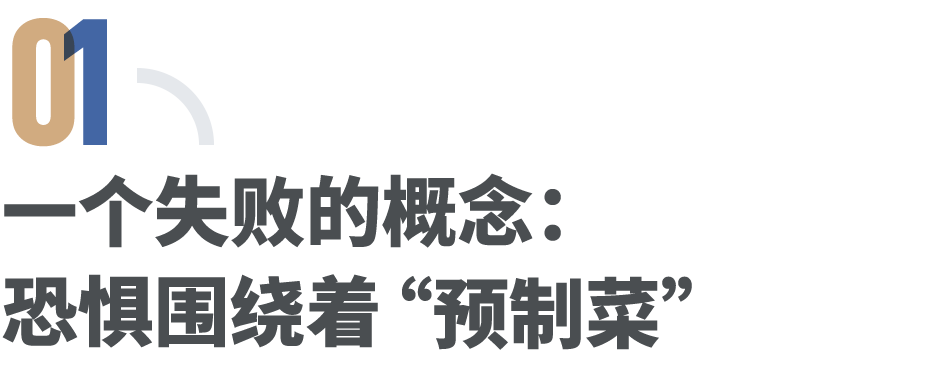
柳业对“预制菜”最早的印象来自料理包。前些年,柳业点过十几块钱的外卖(甚至还有4块钱一份的牛肉饼土豆丝盖饭),吃完就闹肚子。他去网上搜原因,刷到了外卖店的探店视频:一个小作坊,一个微波炉,料理包袋子剪开,微波炉热一下,倒在米饭上就出餐。“店内环境太差,当时就觉得很恐怖,但我想卖这么便宜,可能也只能这么弄”。
和柳业一样,公众对劣质料理包敬而远之。有关料理包的那些视频,比如“廉价外卖速食包的秘密:生产过程令人作呕,日销40万份”,曾在网上热传,涉事公司使用廉价排骨粒,在牛肉中注射大豆蛋白,料理包生产的整个过程脏乱差。
久而久之,在公众话语体系里,预制菜和料理包被划上了等号。
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2023年,“预制菜进校园”遭到多地家长反对。之后,2024年“3·15晚会”报道,安徽省一家预制菜生产企业,用劣质槽头肉代替五花肉做梅菜扣肉。一系列新闻加深了消费者对于“预制菜”的负面认知。

但与公众质疑态度相反的,是资本市场和政府对预制菜行业的大力支持。
云无心说,疫情期间,预制菜的销售情况很不错,投资行业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好赛道,将其捧为风口,“预制菜”这个概念才广为人知。据红餐产业研究院统计,2021年和2022年,预制菜行业均有超过30起融资事件。政府也沿用了这个概念。山东、广东等多地政府,都在疫情期间给出政策支持,争抢“预制菜之都”。
但是,对于什么是“预制菜”,行业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直到2022年6月,中国烹饪协会制定了《预制菜》团体标准,按菜肴加工程度,把预制菜分为三类,即配型(净菜)、即烹型(半成品)、即食/即热型(已完成熟制)。
云无心说,基于这个宽泛的定义,“‘预制菜’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投资界动不动就说‘万亿市场’”。
不过,消费者并不买账。刘鹏是一家活鱼料理店老板,他说:“地方政府、各个协会,都在推广预制菜,大家好像把它当成未来趋势,但是消费者出门吃饭,肯定喜欢吃新鲜的,其实这个矛盾一直没得到解决。”

鉴于“预制菜”这些年在消费者心中留下的负面印象,餐饮企业对外界谈起预制菜,往往是一笑而过、避之不及。“大品牌餐饮老板对于‘预制菜’这个词是非常害怕的,他们不愿意打上预制的标签。”刘鹏说。
今年6月,绿茶餐厅上市之际,创始人王勤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甚至认为有预制菜嫌疑的菜品也都不再售卖了。”在 38元一份的佛跳墙陷入预制菜风波后,绿茶下架了相关菜品,“这些菜品下架以后,我们每家门店都挂出‘本店没有预制菜’的牌子”。
在王勤松的定义里,预制菜仅指“在别的地方加工熟以后冷冻,到店后不需要任何烹饪,加热或不热就可以直接食用”的产品,也就是即热型产品。
这个说法符合2024 年 3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委发布的《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该通知规定预制菜指: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者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
六部委针对上述通知解读称,净菜、凉拌菜、主食类产品、连锁餐饮企业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都不纳入预制菜范围。
和烹饪协会的定义相比,六部委的新规,实质上将“预制菜”的概念重新收窄,仅限于即热、即烹型菜肴。
采用的中央厨房生产的净菜、半成品、成品菜肴,不属于预制菜,冷冻蔬菜不具备菜肴属性,也不属于预制菜,连锁餐饮企业如绿茶、西贝,便都据此认定,门店没有预制菜。但这显然不符合公众心中对预制菜的朴素认知。
在云无心看来,“预制菜”这个术语是一个失败的概念,“一个好的术语,应该有助于理清混乱,‘预制菜’一词反而增加了各方的沟通成本”。一些劣质的外卖料理包,影响了公众对预制菜行业的认知,云无心说,“它已经是一个负面形象,你后面再去圆,再去扩大定义,都解决不了问题”。
9月17日,在西贝预制菜出现争议后,有网友发现,绿茶餐厅悄悄撤下了“本店无预制菜,现点现做”的广告牌。声称“活鱼现做”的太二酸菜鱼,也出来回应“从下单到上鱼仅6分钟”的质疑,消费者才明白,“现杀”并非“现点现杀”,而是事先集中“现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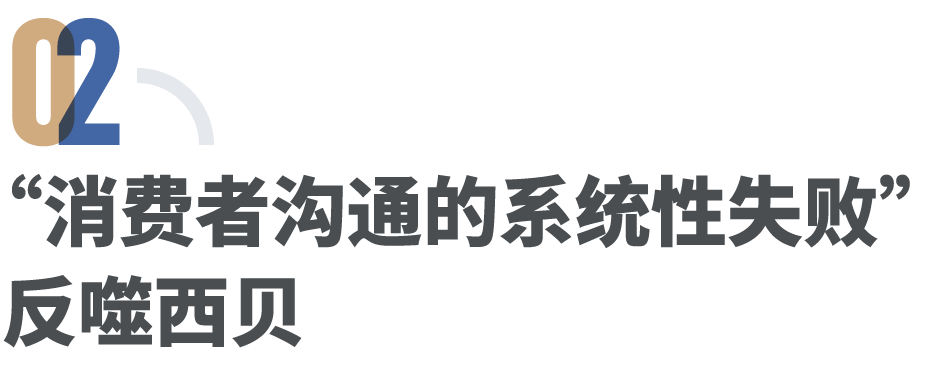
食品科普作者钟凯认为,罗永浩与西贝预制菜之争,背后是“消费者沟通的系统性失败”,他在《关于预制菜,我只说三点!》一文中提到,“正因为预制菜的污名化和话题的复杂性,导致各方都不愿意,也没有耐心去认真做好基础的沟通”。
拿西贝“大翻车”的西兰花举例。媒体在西贝后厨发现,西贝儿童餐使用冷冻西兰花,保质期两年。冷冻、保质期长,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意味着不新鲜。“给一岁的宝宝吃两岁的西兰花”,很多网友在感性上无法接受。但云无心说,这是一个误区,关键问题是,怎么定义“新鲜”?
一种情况是:蔬菜从一个山东农民的农场,运到蔬菜集散中心寿光,再到北京批发市场新发地,然后进入社区菜市场,到老百姓手上。
另一种情况是:采摘当天或第二天,蔬菜进入农村附近的速冻蔬菜工厂,经过清洗、漂烫、速冻后,通过冷链,配送到全国各地。
哪种情况下,蔬菜更新鲜?

老百姓通常认为,刚去菜市场买回来的菜更新鲜,但其实,买回来的菜已经在常温下放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短则两三天,长则十天半个月。科学文献表明,速冻后的蔬菜放置一年,维生素C的含量远高于在常温下放了几天的蔬菜。
“我们在本能上很难接受,但这是科学数据。”云无心说。
云无心进一步解释,食品工业里的速冻工艺,和家用冰箱冷冻是不一样的:漂烫类似杀青,可以使破坏蔬菜营养素的酶失去活性,并消灭大部分细菌,速冻需要在零下20到30度的环境内进行。
除了速冻工艺,软罐头工艺在食品工业里也很常见:对密封好的熟制菜肴,如鱼香肉丝,采用超高温高压杀菌,处理后产品可以在常温下长期保存。
而当看到六部门的通知里强调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时,云无心感到非常无奈。无论是速冻工艺,还是软罐头工艺,都没必要添加防腐剂,“但因为大家有误区,认为预制菜放久了就是有防腐剂,政府为了安抚大家情绪,还得特别强调一下”。
这种“防腐剂有害”的暗示并不利于公众建立科学认知。事实上,食品添加剂对现代食品工业有很大贡献。
国人对食品添加剂的担忧,主要源于过去二十多年,与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鸭蛋、瘦肉精相关的食品安全事件造成的阴影。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食品添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
华立夫从事餐饮行业十多年,现在是一家调味品品牌的创始人。他说,食品添加剂的出现不是污染食物,而是为了让食品更加安全,它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抑菌,二是抗氧化。常见的防腐剂,如山梨酸钾,通过抑制微生物的滋生,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现代人摄入山梨酸钾几乎不可避免,它广泛存在于酱油、料酒、糕点、苏打类饮料中。

华立夫也认为,“预制菜”和“添加剂”的命名都被污名化了。他以烘焙行业举例,面包改良剂也扮演了添加剂的角色,但名字就中性许多。
不过,华立夫也并不期待官方重新给出定义,相反,他认为,政府只要建立健全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严格监管,有效处罚,确保食品安全就可以了,其余的事应该交给市场来决定。
在这些难于厘清的概念问题上,餐饮行业对待消费者的态度除了回避,还不乏“糊弄”。拿袁记云饺举例,2023年9月,有网友在社交媒体曝光,以“现包现卖”为噱头的袁记云饺,使用的饺子皮和馅料都非现做,而是冻品,消费者看到门店窗口有人在现包饺子,实则只是表演。云无心说,“大家好像在各自的表述中取得了一个脆弱的平衡,但一旦有人把这事戳破,消费者就会产生被欺骗的愤怒”。
西贝事件中,不少消费者表示,完全可以接受预制菜,但不接受商家欺瞒,“是预制菜就老老实实和客人说”,重要的是保障知情权。但在西贝创始人贾国龙的认知里,“按国家的规定,我们没有一道菜是预制菜”,他特别向全社会开放了后厨进行直播——也由此陷入舆论漩涡,被这场“消费者沟通的系统性失败”所反噬。

尽管不愿给自己贴上“预制菜”的标签,但实际上,大部分餐饮从业者都认同,预制菜是连锁餐饮的必然选择。
2012年前后,购物中心也即商场在中国崛起。之后十多年,开在商场里的连锁餐厅取代了街边店,成为行业主流。
一位曾在烤鱼品牌“江边城外”任职的开发人员说,“基本上从2014年开始,街边店客流下降,餐饮老板都反应过来,消费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大家都往吃喝玩乐一体的商场走了”。这一年,万达第100家购物中心在昆明开业。不少地方政府清理路边摊的行动,也让街边餐饮进一步萎缩。这位开发人员原来在北京簋街有一家街边店,腾退之后,200平米的店面只剩下40多平,“生意没法儿做了”。
购物中心准备好了迎接餐饮企业,但这里和“锅气”“烟火气”并不匹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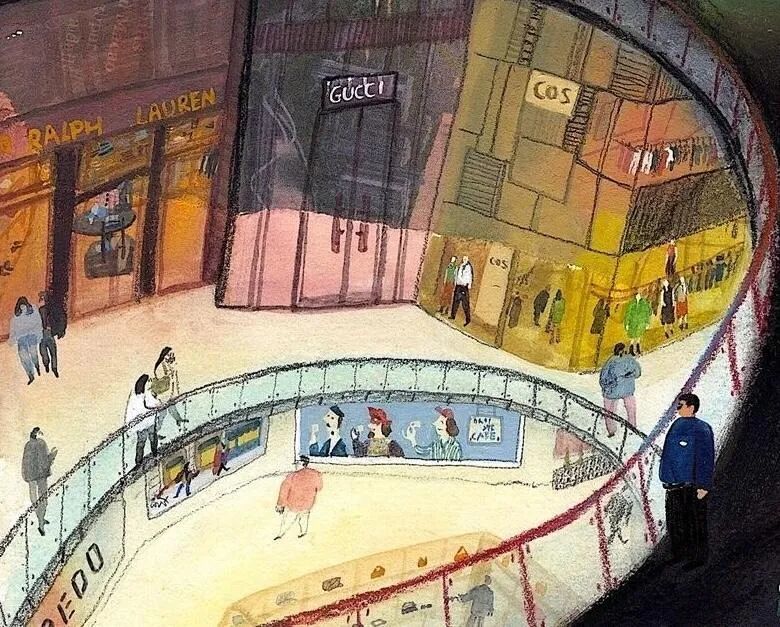
周韦曾是吾悦广场的商业地产设计师。他介绍,一个10万平方的商场,大概会有200个多商铺,开发商会为大部分商铺预留标准化物业条件。但餐饮中的重餐(与轻餐相对),也就是具备“明火现炒”条件的传统餐饮,对物业的要求是超出标准配置的。因此,一般来说,重餐铺位极为有限,只占餐饮铺面的1/3到1/2,它们面积在300平以上,分布在商场的顶层或次顶层——这里具备最优排烟条件。
周韦说,商场不能用明火是谣言。区分轻餐和重餐的关键,就是看餐厅后厨是否具备燃气以及排油烟条件。
不过,尽管商场给重餐饮区预留了燃气管道,但多位从业者表示,考虑到各种成本,开通燃气的商铺并不多。一位曾在西安万达工作的招商人员说,“在西安这边,接个燃气表10万起步,前期费用非常高”。为了满足消防合规性,后厨还要规划出独立的燃气间,用耐火隔墙、防火门,隔开燃气间与厨房。建设燃气间的投资,其占用的租赁面积,也是实实在在的空间成本。
一切都是成本和效率的计算。从商场角度,周韦说,时间成本也限制了商场选择的余地。吾悦广场从设计到开业,两年时间,留给招商的时间至多只有10个月。这10个月里,要把60个左右的餐饮铺位招满,商管在挑选客户时,会优先选择满足当前物业条件且装修速度快的轻餐。周韦说:“问题不仅在于租金,更在于空间效率。”
疫情之前,商场招商如日中天,租金年年上涨。彭国生在2016 年进入这个行业,他说,那会儿“每家生意都能挣钱”,品牌抢着进商场,招商非常容易。与之相对,街边夫妻店几乎不可能进商场。
彭国生说,小老板不具备运营能力,无论是营销能力,还是前厅后厨的管理能力,他们难以适应商场的快节奏。一天两餐,午市和晚市,商场希望餐厅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创造尽可能高的单平米效益。
西贝这类具有特色的品牌连锁完美契合了商场需求。彭国生曾在多家购物中心工作,他以西安万达举例,西贝在万达属于A类店:全国连锁且均为直营门店,自带客流;西北菜,扩充商场餐饮多样化;客单价 90 元左右,可拉高商场餐饮的整体客单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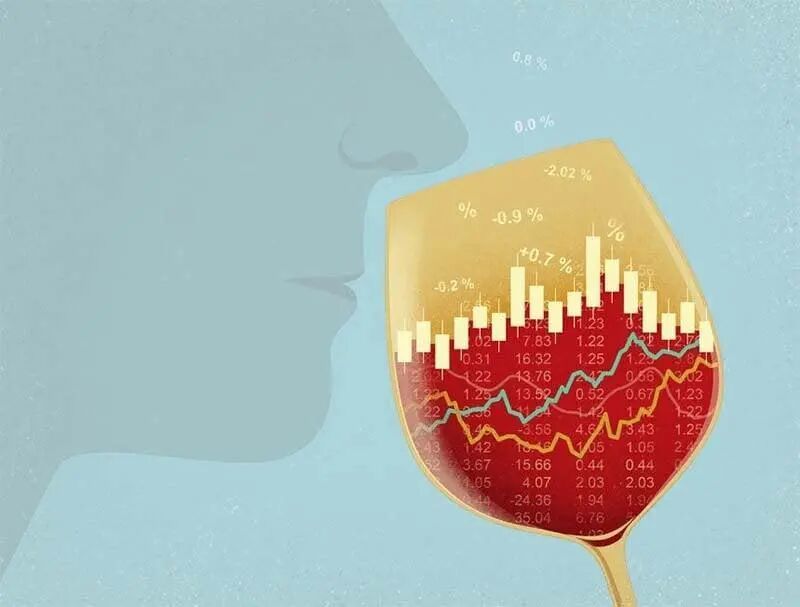
在购物中心蓬勃发展的那几年,连锁餐饮品牌享受到了红利,所谓“战略合作”,二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出于扩大规模的野心,还是为了覆盖连年增长的租金、人力成本,连锁餐厅选择预制菜是难以避免的趋势。
预制菜首先解决了中餐连锁化最大的难题:人的难题。
左太明是一家湘菜品牌创始人,他坚持菜品现做,店主要开在街边,也“迫不得已”进过商场。他说,对传统中餐来讲,食材新不新鲜是其次,厨师才是决定一道菜口味上限的关键。过度依赖高素质的厨师团队,严重限制了中餐品牌的开店数量。另一位活鱼料理品牌老板刘鹏也提到:“餐饮管理里边,人是最不稳定的因素,也是我们开餐厅最头疼的事,厨师心情好或不好,炒出的菜味道可能都不一样。”
预制菜的出现,帮助连锁餐厅完成了“去厨师化”。当“适量、少许、火候”量化为“800瓦慢炖20分钟”,一个没有多少经验的厨师也能很快上手。
一旦口味标准化、定量化,后厨效率也能得到显著提升。根据招商银行研究院的测算分析,通过中央厨房简化后厨操作、后厨面积缩减,可为餐厅带来6%-8%的利润率提升空间。
过去,资本市场很少青睐中餐:传统中餐的商业模式离标准化、可复制、高增长非常遥远。2019年前后,情况发生变化,资本大量涌入餐饮行业,给出了超出传统餐饮人认知的估值。左太明说,行业的蓬勃,正是得益于预制菜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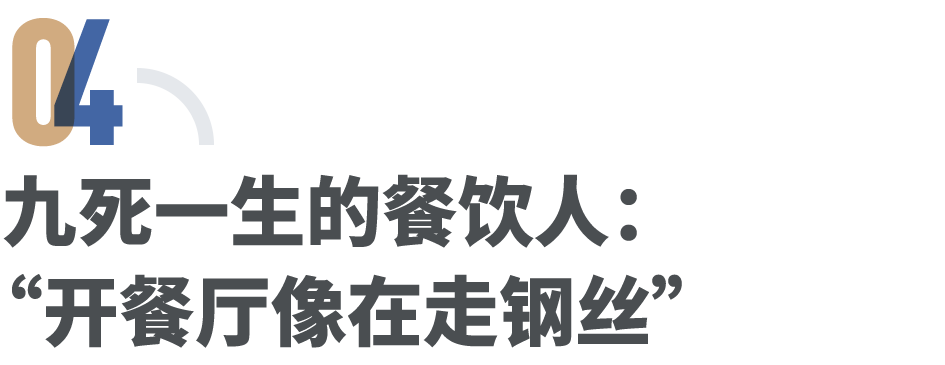
刘鹏开了十多年活鱼料理店,遭受的最大打击并非来自疫情,而是2023年日本核废水事件,“直接把我所有店都给干没了”。因为这段经历,他完全理解贾国龙对峙罗永浩时的不理性,“开餐厅像在走钢丝,老板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活鱼料理店,没有炒菜,不需要用明火。刘鹏只在深圳的一家分店开通过燃气,结果却总在为此焦虑,“我经常担心,万一员工下班没关阀门怎么办?”
聊到让西贝栽倒的冷冻西兰花,他认为,“新鲜西兰花和速冻西兰花各有优势,新鲜的肯定更好吃,速冻的更好控。工厂化清洗肯定比饭店洗的干净,农药残留更好追溯”。他在自己的店里很少用带叶的菜,怕洗不干净,“你有良心,你盯着菜叶洗,也有可能有个虫子你没看清”,取而代之的是西葫芦,清洗方便,加上削皮,很容易处理干净。
现在,除了疫情、食品安全,餐饮老板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还要加上公关危机。

与公众不一样,很多餐饮老板在贾国龙翻车后,仍然力挺“贾老板”。华立夫认为,贾老板的翻车,与其说是品控问题,不如说是公关问题。企业出了信任危机,首先一定是道歉,解决情绪问题,但“西贝老板没有公关意识和形象管理意识,他在自己的情绪上,其实不能完全理解不同的消费者,他们到底在吵什么”。
华立夫觉得,有关预制菜的争议说到底是情绪问题和认知差问题,只要西贝还有人排队,就说明还是有消费者愿意为西贝的安全属性、标准化服务付相对高的溢价。
2014 年,西贝展示全开式明厨,是业内先行者。刘鹏仍然记得,十年前,第一次在商场看见西贝明厨亮灶时,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整个厨房都是透亮的,它的面点房、凉菜间各方面我都能看到,我说这太厉害了,这是高手设计的厨房”。
透过这里,刘鹏清楚地看到了西贝在食品安全上的投入。他以凉菜举例,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制作凉菜需要专人在专间负责。专间大概10平方的面积,以300元/平方/月的价格计算,一个月就多出了3000块钱的房租。刘鹏经常吃西贝凉皮,一份定价39元,“它很贵,但是我吃那么多次,没拉过肚子”。
在商场工作的彭国生也去过西贝后厨检查,“抽油烟机每天都在擦,咱们家里厨房也做不到这种”。也因此,他经常带孩子去吃西贝儿童餐,作为家长,他觉得西贝儿童餐的搭配做得很不错,有主食、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汤,很齐全。至于服务,他感觉西贝的服务员几乎有求必应,甚至还能主动给宝妈抱娃——高素质的服务背后也是人员成本的投入。这些细节支撑着他在预制菜事件后仍然力挺西贝。
在与罗永浩的交锋中,西贝老板贾国龙曾称,“我们的账不怕查,利润大约为 5 %”。
多位餐饮从业者向凤凰网表示,这个数据应该是符合真实情况的。
“西贝在食品安全上是比较舍得投入的,餐饮行业的人基本都知道,不然不会在食品安全方面帮西贝说话。”刘鹏说。他经营的餐厅主打活鱼,“一部分消费者喜欢高品质活鱼,我就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但这个定位很窄,细分人群很少”,但“老板各有各的道,各的各的追求”,从创业层面,他佩服贾国龙。
人们对贾国龙在疫情第二个月喊出的“疫情致2万多员工待业”、“贷款发工资也只能撑3个月”等危机言论记忆犹新,但很少注意到,贾国龙在后来复盘,大疫三年,他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中餐现代化”。

疫情期间,贾国龙推出了西贝儿童餐,以及有零售属性的预制菜快餐品牌“贾国龙功夫菜”。202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国龙把麦当劳视为餐饮行业现代化的典范,并表示,“西贝在正餐方面有 300 多家店,如果没有标准化,我也开不出300多家店,我本人做企业还是追求大规模化”。
不过,贾国龙在功夫菜快餐上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2024年,他砍掉了折腾快十年的快餐业务和零售业务,回归到正餐业务。
这次风波对西贝的暴击不亚于疫情。多次发声却越来越深陷泥沼后,9月28日,人们发现贾老板默默清空了多个社交账号,不再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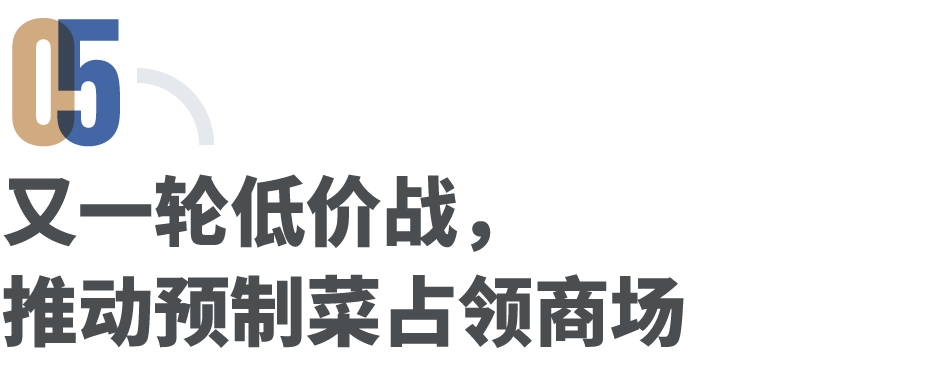
虽然餐饮人愈发缄口不语,事实上,预制菜已经深深渗透我们的当代生活了。
在商场吃一顿现炒的中餐正餐需要花多少钱?一位餐饮从业者给凤凰网粗略算了一笔账。
以绿茶为参考,2024年,绿茶餐厅客单价56.2元,每日翻台率3.0,日销售额21700元。这是绿茶和第三方食品加工厂合作之后的业绩。在招股书里,绿茶提到,招牌菜如绿茶烤鸡,由第三方食品加工厂提前制备,厨房员工仅需要用预制酱包腌制鸡肉,并将其放进烤箱,烘烤一段时间,便可上菜。
现在,假设有一家经营模型和绿茶相似的商场餐厅,放弃了食品加工厂,把食材交给厨房员工自行洗、切、配。首先受到影响的,是翻台率。几乎所有现炒餐馆都有出餐慢的问题。当客人的就餐时间从60分钟,提升到80分钟,翻台率大概会从 3.0 下降到 2.25 。
这时,为了保证同样的收入规模,客单价需要提升至75 元。
如果再考虑到现炒增加的员工成本——有经验的厨师、洗菜员等,以及空间成本——后厨面积扩大,客单价可能得涨到100元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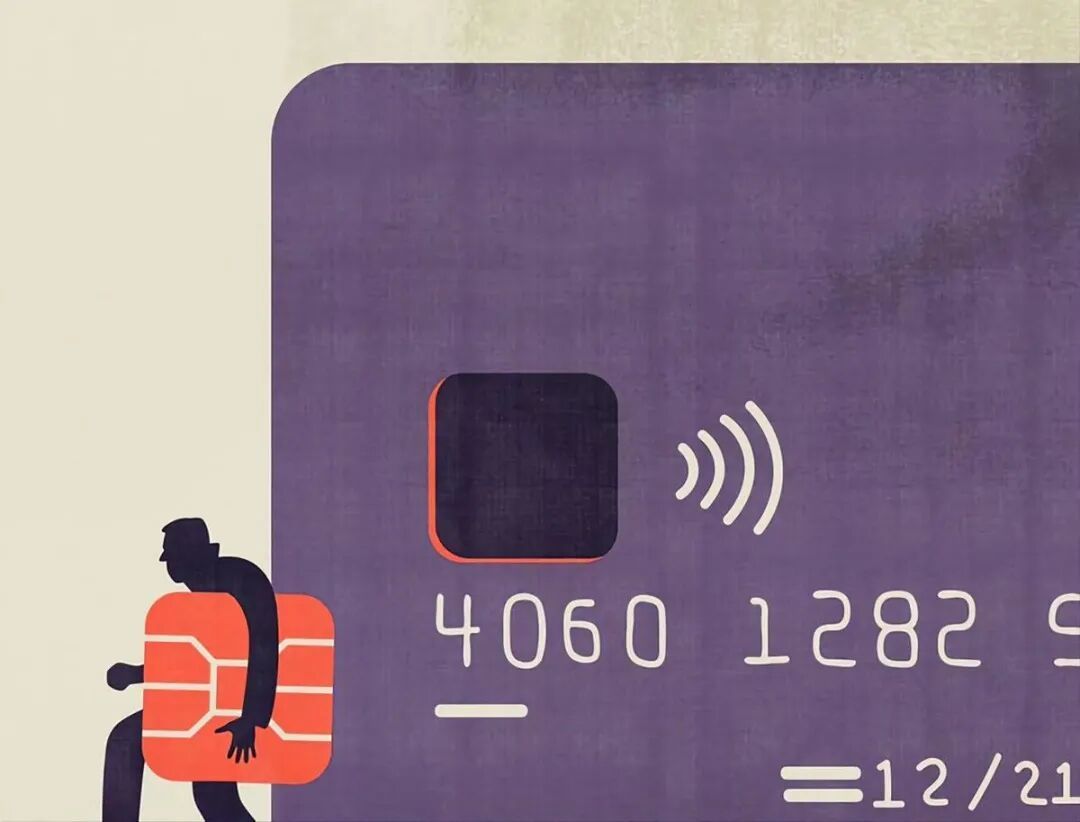
根据招商银行研究院的测算,中央厨房可为连锁餐厅带来10%-12% 的利润提升空间。可以对比的是,2024年绿茶餐厅的净利率为 9.1 %,如果不依赖第三方食品加工厂,餐厅将面临亏损。
这可能与一些消费者的印象不同:在竞争充分的餐饮行业,连锁餐厅使用中央厨房降低的成本,早已在价格上有所体现。一位商场招商人员直白地表示,如果没有中央厨房,大多数人可能吃不起商场里的饭。
不过,现在去商场吃中餐正餐还是比前两年更便宜了。2024年下半年,连锁品牌开始打起了低价战。
左太明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哪怕是在疫情期间,一线城市的餐厅都还能活得不错,虽然有封控,但大家的消费信心和预期还是向上的——那时房价还没暴跌,消费也没有降级。2024年,他开在商场里的分店,推出了308元的双人团购套餐,“说实话我开店我快11年了,去年才上了大众点评的套餐,实在是不做不行”。如果继续亏损,这家店就只能倒闭。
低价战一来,进一步推动了预制菜占领商场。问题是:更便宜了,为什么还是骂声一片?
一方面是因为,“预制化程度越高,一定是越来越难吃,”刘鹏说。
另一个原因是行业不透明,消费者没有知情权。许多人以萨莉亚举例。作为“预制菜骨灰级玩家”,萨莉亚不但没被骂,反而深受追捧,原因是:低价,并且明确标示速冻食品,“生怕你不知道他们有预制菜”。
西贝事件后,国务院食安办表示,已牵头多部门加快推进预制菜国家标准的制定,大力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更好维护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

不过,云无心认为,让市场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发展,也能实现消费者和餐饮行业共赢的局面,愿意公开透明的餐厅自然可以吸引消费者,“非要政府、行业、餐馆采取什么行动去改变什么,没有必要”。
云无心建议:“回归到餐饮的本质,无论是净菜配送、预处理食材、烹饪半成品,还是预制成品料理包,它们都只是餐饮供应链上的不同环节和技术,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用本来的特征名称。”
未来,消费者会怎样用嘴投票呢?
刘鹏说,人们会回归家庭,“过去,出门下馆子是改善生活,现在反了过来,在外面吃是应付一口,在家吃才能改善生活。”
左太明相信,人们会选择精品小店。在连锁湘菜品牌客单价普遍低于50元的情况下,他的店维持着150元以上的客单价:这是请大厨、用新鲜食材、做时令菜的必然成本。他觉得,总有那么一些客人,会愿意来店里体验。
还有人回归街边摊,比如投奔这个国庆爆红的景德镇“鸡排主理人”。鸡排哥秉持着自己的经营原则:四点半后不接散客,只卖学生,卖学生比散客便宜1元;“新鲜采购”、“自己腌制”,真诚敞亮,不绕弯子,全是烟火气。在人们眼中,这些路边摊的存在,成了一路狂奔的预制餐饮品牌的反面。
应对方要求,文中柳业、周韦、彭国生为化名
作者 王雯清 | 编辑 周褶褶
排版 魏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