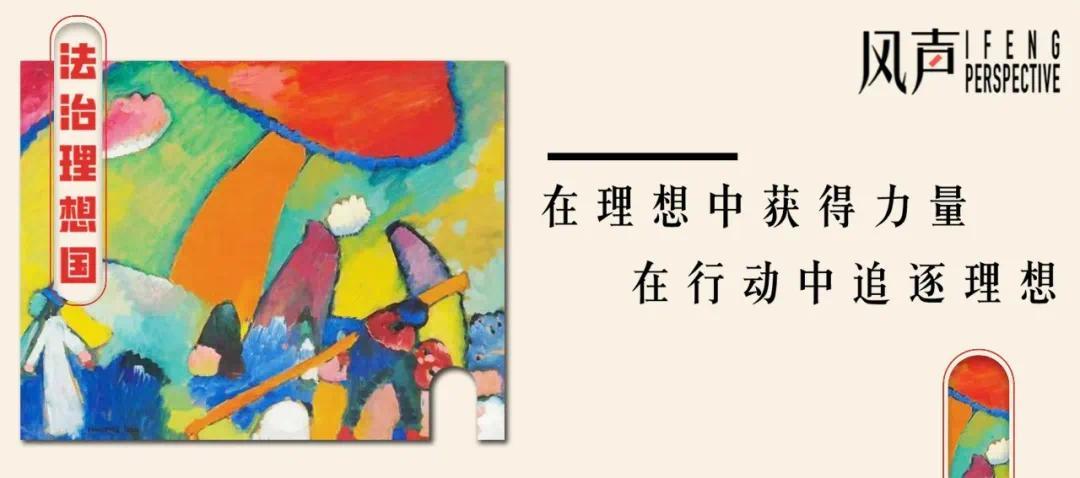风声 | 刑法第二十一条也是可以拍电影的
风声,那是一种神秘而又充满力量的声音。在刑法的领域中,第二十一条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熠熠生辉。它就像一道指引正义的光芒,在法律的黑暗中照亮前行的道路。可以想象,一部以刑法第二十一条为主题的电影,将展现出法律的威严与人性的复杂。电影中,风声呼啸,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法律守护和挑战的故事。它会让观众深刻感受到法律的力量与温度,引发对正义和人性的深刻思考。这部电影或许能成为法律题材中的经典之作,让更多人了解和尊重法律。
作者|罗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一则新闻引起了民众关于紧急避险的讨论。对于紧急避险,刑法第二十一条有三款规定:
第一款,对紧急避险做出了定义:“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款,规定了避险过当:“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三款,则规定了不适用紧急避险的情况:“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与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不同,紧急避险的本质是正对正,行为人通过损害合法权益来保护合法利益。但正当防卫则是正对不正,行为人对于不法侵害进行防卫,损害了不法侵害人的利益。所以,法律对紧急避险的限制更多。比如,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保护的利益,否则即为过当。
但在正当防卫中,行为人造成的损害可以等于甚至大于被保护的合法权益。比如张三为了避免性侵将他人打死,虽然性自治权的利益小于生命权,但这仍然可能构成正当防卫。但如果行为人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牺牲他人生命,无论如何,这都不构成紧急避险。因为生命权是不能比较的,没有谁的生命比他人高贵,即便你的智商250,你的生命也和智商25的人是一样的。
多年前,我在一个地方上课,一个学生睁大眼睛问我:“老师,如果我快饿死了,真的可以吃大熊猫吗?这真的是紧急避险吗?”我说:“对啊,因为人的生命大于动物的生命啊。”学生大惑不解:“但熊猫是国宝啊!”我说:“但你是无价之宝,你是人啊!”学生小声说:“但我并非著名大学毕业,没有考上研,法考也考了好几次,男朋友也和我分手了,家里人都说我是废物,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说着说着,她都快哭了。我对她说:“即便所有人都认为你没有价值,即便你自己也认为你一事无成,你依然是顶天立地的人,你依然比所有大熊猫都宝贵。”
另外,紧急避险必须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而正当防卫则没有这一条件的限制:为了鼓励民众和不法侵害做斗争,防卫人即便还有其他选择,但决定迎难而上和不法侵害人干到底,这也属于正当防卫。
然而,紧急避险要成立,则还是需要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铤而走险。只是在判断何谓迫不得已时,不能采取事后诸葛亮的标准,而要站在当时的情境中作出合乎一般人良知的判断。
因为紧急避险涉及利益权衡,要求所保全的利益大于所损害的利益。所以,一旦出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不少人都会认为公共利益自然大于个人利益。
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年前的姚丽案。1999年某储蓄所遭到两名劫匪抢劫,在报警未果的情况下,职员姚丽与之周旋,劫匪用刀逼姚丽打开银行专用箱拿出13568.46元,实际上保险柜中还有25万元,钥匙就在姚丽手中,但她谎称保险柜里没有钱,最终保护好了25万元的存款。案后第二天,姚丽还从自己家中取来现金13568.46元交给了单位。
姚丽虽然以较小的损失保护了银行巨额财产,却因“未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而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姚丽认为银行开除决定不当,向法院提起劳动诉讼。法院判银行败诉,认为姚丽已经尽到了一定责任,不构成严重失职行为。姚丽重回银行工作,但银行又向姚丽宣布了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大过处分。事后,银行要求全体员工要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与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斗争,不惜一切保护好国家资产和财产安全,并且规定畏缩不前、拱手交出国家资金和财产的要处以罚款、处分以及刑事责任。这个案件当时引起了民众的广泛讨论,人的生命权高于财产权,无论财产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生命至上”这个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另一个典型的案件,是醉驾送妻就医案。深更半夜,妻子突然发病晕倒,因住地偏远,救护车不能及时赶来,醉酒丈夫陈某在无奈之下开车将妻子送往医院救治,被警方当场查获。这个案件后来以危险驾驶罪起诉到法院,但法院直接以紧急避险宣判无罪。
考虑到这类案件并不少见,所以202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还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对紧急避险做出了规定:“醉酒后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不得已驾驶机动车,构成紧急避险的,依照刑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理。”司法意见甚至还规定,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符合条件也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司法意见的精神是让法律符合人的常情常理,法律不是冰冷的刚性条款,它是应该有温度的。如果成立紧急避险,自然是正当行为,不构成犯罪。即便不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比如孩子高烧39度,父亲刚喝了点酒,觉得叫救护车会耽误时间,所以直接送孩子去医院,即便认为不属于迫不得已的,但也可能不构成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规定了紧急避险,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虽然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处罚法这些行政法中,没有像刑法那样直接规定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条款,但法律的精神应当保持一致。事实上,在行政法规中也有不少紧急避险的规定。
比如,《渔业港航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5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以紧急避险为目的的行为,可免予处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2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证据证明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险造成,经核实的,应当予以消除。
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中规定了正当防卫:“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是,对紧急避险没有规定。考虑到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生效,公安机关也将出台新的规范,届时也许可以考虑对紧急避险做出相应的规定。
这段时间,我在写一篇和淫秽物品有关的学术论文,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道德主义,尤其是康德对人的尊重能否独立作为刑事惩罚的依据,比如淫秽物品是对于人的物化,所以应该予以惩罚。后来我慢慢发现,虽然我偏爱康德,却明显产生了误读,因为康德道德律令主要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他律;以法律惩罚的他律形式来推行自律的道德,似乎是对康德哲学的背离。
康德将责任区分为合乎责任与出于责任两种:为了某种利益而遵循道德,这是合乎责任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则是出于责任的。虽然从外表来看,出于责任和合乎责任是完全一样的,但两者的内在动机是不同的。因为害怕惩罚而遵守道德合乎责任,但并不一定出于责任。相反,如果没有任何世俗奖惩的刺激仍然愿意遵守道德,或者即便面临着惩罚,仍愿坚守道德,这才是出于责任,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
所以,康德认为,经验世界充满着令人作呕的大杂烩,人类的经验无法作为道德的根基,否则道德标准必然摇摆不定。如果只是着眼于可见的经验,人要获得心灵的安定,唯一自洽的选择就是妥协与自欺,否则内心的冲突是永无止境的。如果要告别自欺,只能把道德准则的依据放在超越经验的洞穴之外,人才能真正自洽,真实地过一种心安理得的生活。
正确就是正确,而无需顾及善行的世俗结果,无需绞尽脑汁地权衡利弊。康德如是言之:“道德本来就不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趋利避害只是动物世界的法则,但义无反顾才是人类社会应该提倡的价值。
去年春节有部电影叫做《第二十条》,探讨的是正当防卫。其实,“第二十一条”也可以拍成电影——真实案件远比电影剧本更精彩,更令人深思。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 | 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