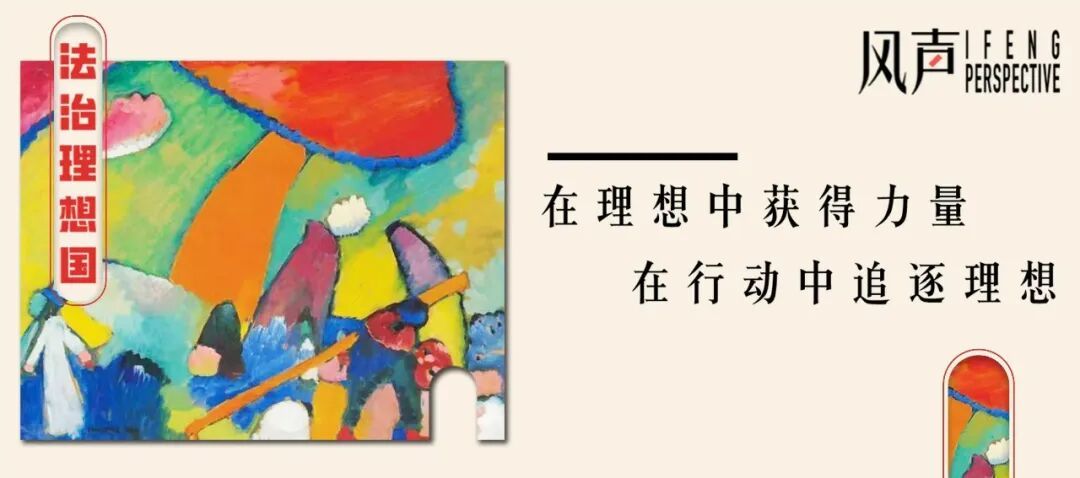风声|“严禁侮辱大龄未婚女性”,算不算另一种歧视?
作者|陈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禁止诋毁、侮辱大龄未婚女性”,这一宣示性立法出自近日修订通过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21条,它迅速引发了网络热议:这也值得立法吗?为何只保护大龄女性,不保护大龄男性?
最近一段时间,有不少省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针对现实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侵害女性权益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治理。尤其山西省明确否定“剩女”等贬损标签,重申妇女继承权与男性平等,不得以风俗、婚姻状况为由剥夺女性继承权,有不少条款可圈可点。
为何就这条禁止歧视大龄未婚女性的规定冲上热搜?这条政治上绝对正确的法条,为何隐隐让人不安?在立法之后,女性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行动呢?

只保护女性是对男性不公平么?
直接的批评,来源于“只保护大龄女性,不保护大龄男性,是否构成性别歧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这个法规是在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背景下提出,重点关注的必然是妇女权益问题;其次,我国宪法规定了“男女平等”,但现实中仍然存在针对女性的传统偏见和歧视。与女性所面临的系统性、结构性的性别歧视相比,男性困境的性质和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才需要通过专门的制度和政策来保障妇女权益,纠正这种权利失衡的状况。
具体到这一规定本身——“严禁诋毁、侮辱大龄未婚妇女”,众所周知,我国35至49岁群体中未婚男性比例远超女性,但大龄未婚女性面临着职场歧视和家庭催婚等情感困境,被贴上“剩女”等负面标签,这种特殊保护是合理的。当然,现代男性也遭遇了身份和情感困境,有不少大龄未婚男性被贴上“非自愿单身者”的标签,暗指他们是社会竞争和情感关系中的失败者,不配拥有婚恋的幸福。
本法条的宣示性态度,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漠视,而仅仅是为了保障女性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改变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推动形成更加平等、包容、多元的婚恋观。

正如本栏目不久前讨论过“福建省的妇女权益保障条例里规定妻子可查丈夫财产,却没有规定丈夫的同等权利”,如赵宏老师所言,这一条款仅为落实“妇女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知情权以及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能武断地认为仅规定女性可查询配偶财产有违宪法上的男女平等。
与此同时,在第21条“严禁诋毁、侮辱大龄未婚妇女”的后半段规定了“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或者残疾婴儿的妇女以及不育妇女”,这更加令人不安。这说明,男尊女卑、把女性视为生育机器的前现代观念,仍然是现代中国女性面临的困境和障碍。
法律总是倾向于反映现存的权力结构,口号的平等不等于实质的平等,立法的平等不等于现实的平等。
从立法的态度看,现代社会这种权力结构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可以享有无须法律赋予的种种权利,而女性则需要法律特别赋权。因此,在男女平等的意识并未获得充分贯彻的地方,立法必须回应女性权利保护的要求。这也构成了上述立法道德正当性的基础。

严禁歧视也是一种歧视?
我国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性别话语,影响和塑造了我们的上一辈。但他们对于“男女平等”,往往只在口号上重视,内心却倾向于漠视。一提起男女平等,就有很多男性会反问:难道现在还不平等吗?还要怎样平等?而老一辈的女性则会认可:已经比解放前好了不知道多少了,慢慢来吧。
对于本条款上热搜,则更加反映了事实的不平等。因为宣示性的立法表达的是某种价值导向、政策立场或道德要求,但因缺乏具体实施机制和法律责任,无论是倡导还是禁止,它所指向的行动都是无力的。
我们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什么呢?国家的保护性立法和宣示性立法,为什么会让人不安?它是否引发了一种无力感?针对前文所述的条款,我们会进一步发问:为什么会有大龄未婚女性?这是自由选择吗?如果是,为什么会对这样的自由选择进行歧视?
在追问之下,我们会发现一个事实:大龄女性未婚的“自由”,在传统择偶婚配观念以及现代性的双重作用下,显得苍白无力。女性获得的只是择偶自由,却没有匹配“自由择偶”的环境。女性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对象作为欲望和爱恋的对象,这早已被写进了文化基因。“男强女弱”“男大女小”的传统婚配观念主导着女性的择偶观,号称“解放”和“平等”的妇女却对基于真正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性别角色表现出茫然甚至抗拒。
这一条款除了揭示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大龄未婚女性的歧视并非单纯的个别现象,而是父权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交媒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还可能固化了一种女性的弱者叙事,这是一种隐藏得更深的歧视——“有的女性太惨了,大龄没有人娶,老了也没有孩子”。将女性置于弱者的地位,意味着男人比女人强,女人需要拯救和保护。

与之类似的,对女性的过度赞美,会使普通女性不得不和一个并不存在的完美“自我”做斗争。不论是“捧杀”还是“弱女”,都构成对女性主体性的伤害。
这说明,靠立法和宣言解放女性是不够的,解放意味着赋权,但拥有权利并不意味着使用权利。
即便法律一遍遍确认,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提升了,却没有带来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的改变。而性别意识形态不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分工模式不改变,女性就无法在择偶中和男性处于同等的地位,这就无法实现基于平等的亲密关系。对此,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慢慢来要等到什么时候?

从弱女叙事走向行动叙事
为了实现矫正正义,国家的保护性和宣示性立法当然正确;作为被保护者,指出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是不是不合时宜呢?
实际上,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女性主义,都反对将女性始终描绘成无辜、无助的形象,认为这本身就是在解除女性的武装,否定了她们的内在力量。存在主义和女性主义倡导的,是从受害者叙事走向行动者叙事。

本栏目讨论过家暴、性侵和职场歧视等议题;在家庭和职场领域,不局限于女性受害者叙事是必要的,这不是否认伤害,而是将叙述的重点从“他们对我做什么”转移到“我如何抵抗”“我如何重建”。这需要一种比抱怨更艰难的勇气——直视自身,并为自己命运负责的勇气。这也需要对保护者和拯救者(往往是男性形象)说,“谢谢,我试试自己来”。
这种勇气是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觉醒,也是真正走向性别平等的象征。如前所述,我国立法规定的“平等”,是国家解放妇女的后果,而非妇女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男性”给予“女性”的“平等”——可是,你想要和他平等,怎么可能让他给,而不是自己去拿呢?
如今,女性的解放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手里。大龄女性要不要焦虑、不婚不育的人生是否不完整,职场女性如何平衡家庭生活与事业发展……这些都是女性应该做出的回答,而不应由男性定义。在“严禁歧视”的宣示性立法之后,我们需要的是,如何重建,如何生活。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