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巴士APP跳出低俗成人广告!客服仅以“审核疏忽”为由,就能免责吗?
近日,有网友反映,在打开宝宝巴士旗下一款“宝宝巴士儿歌”APP时,开屏会跳转到含有成人内容、低俗擦边直播等不适合儿童观看的第三方广告,引发家长担忧。
该网友称,这部手机平时主要由孩子使用,近期发现手机中无故多出多款陌生软件,之后才发现可能是孩子在APP内误点广告所致。该网友还认为,孩子因难以识别广告跳转选项,容易误触进入不良页面甚至自动下载无关软件,可能受到不良引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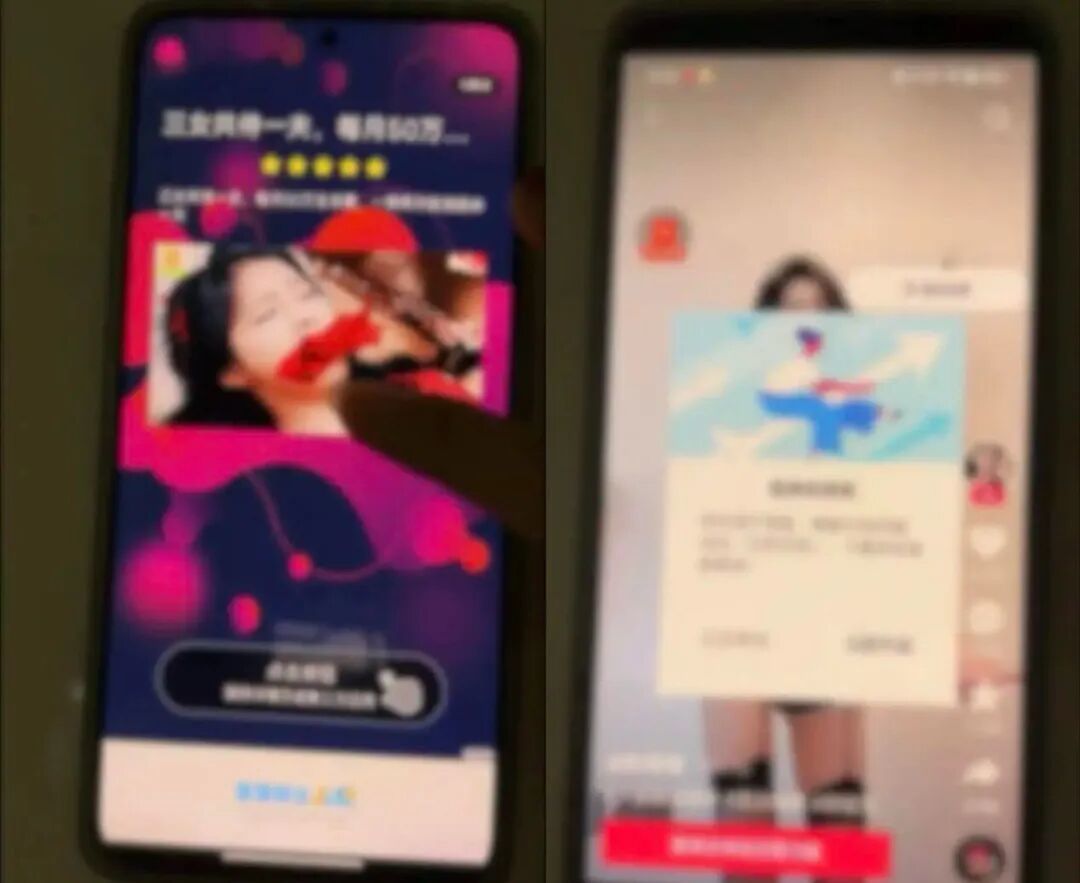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相关话题的评论区中,一位来自云南的家长反馈,“在未曝光之前,孩子在玩宝宝巴士APP时,不知点击到哪里,平板被各种广告霸屏,关都关不掉,就像中病毒一样。每次我都只能强制按重启键或者关机。”
10月28日,宝宝巴士客服称,非会员APP会展示第三方广告且平台会审核,但审核或有疏漏,低俗广告属“异常情况”,将反馈技术部门排查。10月29日,宝宝巴士公司发声明,对APP跳转不良广告高度重视并致歉,已下线相关广告、停止合作,且开展全面自查自纠。

受访专家认为,此类广告不仅包含涉嫌擦边的成人内容,还通过隐蔽跳转选项诱导儿童误触,既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当前分散、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已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儿童数字生态,亟需从“原则性禁止”迈向“精细化治理”。
1、该App主要面向儿童群体,推送低俗广告的行为涉嫌违反哪些法律规定?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在法律定性层面,‘宝宝巴士儿歌’作为一个明确以低龄儿童为主要用户群体的应用程序,由于低龄儿童对相关的网络信息缺乏判断能力,该应用程序的经营者应当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其向未成年人推送低俗广告,显然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相关规定。”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叶刚指出,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规定为首要的立法目的,该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了“网络保护”,该章的核心立法目的是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并且明确规定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危害其身心健康的信息。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进一步补充,从广告法视角看,该行为违反广告法第九条关于禁止淫秽、色情内容的规定。
“宝宝巴士儿歌APP推送的低俗擦边直播广告,其内容明显属于广告法第九条第(八)项所明确禁止的‘含有淫秽、色情内容’。该条款是广告内容的底线红线,无论面向何种受众,均不得触犯。”姚金菊说。
她分析指出,广告中跳转选项难识别,易让儿童误触不良页面或自动下载软件,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与知情权。儿童及家长使用免费儿歌APP时,有权知晓广告存在、形式及点击后果,而难识别的跳转选项本质是隐瞒误导,会让认知不足的儿童无法获知点击真实后果,进而被剥夺知情权。
“自主选择的前提是充分知情。由于知情权被剥夺,儿童在误触广告时的‘点击’行为,并非其真实意愿的表达,更不是一种‘自主选择’。平台通过难以识别的广告页面跳转技术设计,使儿童在非自愿、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引导至其他页面或下载软件,诱导用户完成其本不会选择的操作,剥夺了其‘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的权利,其自主选择权受到了严重侵害。”姚金菊说。
对此,《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理主任吴学联表示,广告中难以识别的跳转选项,使儿童容易误触进入不良页面或自动下载软件,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和第九条关于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规定。同时,消费者可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四条,通过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举报,向平台反馈、请求消费者协会介入等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共同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2、作为广告发布者,平台对第三方广告内容是否负有审核义务?平台是否能以“审核疏漏”为由免责呢?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看来,平台作为广告发布者,需承担广告内容的审核与把关责任。对于以未成年人为主要使用群体的APP,即便暂不明确其是否属于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制的“以未成年人为服务对象的在线教育网络产品和服务”(该类产品明确禁止插入网络游戏链接、推送与教学无关的广告),其运营者仍负有广告审核义务。
“平台以‘广告来自第三方供应商’为由推脱责任不成立,其应通过内部管理、技术管控及内容审核机制规范广告推送,第三方行为不得作为其免除责任的借口。”刘晓春说。
姚金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强制要求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审核制度并核对广告内容。这是一种事先的、主动的审查义务,是广告得以发布的前置条件。宝宝巴士APP作为广告发布者,此义务是其运营的法定前提,无可推卸,不能因为广告来自第三方而转移或免除,对其“明知或应知”的违法广告予以制止。这意味着,平台的责任是持续性的,不仅限于广告上线前,更包括上线后的持续监督。
“‘应知’是指一个合理的、谨慎的主体在同等情况下应当知道的事实。一个面向儿童的APP,其广告审核理应采用最高标准。对于低俗内容,平台以‘疏漏’为由声称不知,是站不住脚的。在此特定场景下,平台应当知道其审核责任重大,应当能发现并拦截此类明显违规内容。因此,‘审核疏漏’使其从‘不知’的潜在免责状态,直接落入‘应知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明确担责状态。”姚金菊进一步分析道。
对于此类行为的责任划分,姚金菊表示,发布违法广告的源头责任在于广告主。当平台“明知或应知”广告内容侵害消费者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时,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如平台无法提供广告主的真实有效信息,消费者有权直接要求平台先行赔偿。这倒逼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合作方资质,履行广告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的义务。
3、对此类问题,如何加强监管明确广告内容、投放方式及审核标准,更好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此次事件不仅暴露了宝宝巴士对第三方平台的审核问题,也揭示了儿童类APP接入第三方广告平台后的广告监管治理问题。
在王叶刚看来,有必要出台专门针对儿童APP广告的监管规范,平台也应当建立更为有效的管理机制。我国民法典、广告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虽然对广告的内容、广告的发布、广告的审核等作出了规定,但相关规定并没有充分考虑儿童权益保护的特殊性。考虑到儿童对相关的广告内容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有必要对其进行特别保护。
具体而言,他认为,例如可以对向儿童类APP推送广告的类型和内容进行限制,从源头上防止不良广告进入儿童APP;或者严格规范广告的展示形式,禁止诱导点击行为,确保“关闭”选项清晰、有效等;或者对儿童类的广告进行前置审核或备案制度,以有效规范儿童类APP的广告推送行为。
姚金菊建议出台儿童APP广告监管规范,具体分三方面:一是明确广告内容“负面清单”,纳入隐性危害内容,同时推行“合规广告” 认证并严审广告库;二是立法禁止欺骗性界面、自动跳转和无声下载,要求儿童广告有清晰标识与认证标志;三是规定12岁以下儿童APP广告需按“未成年人模式”最高标准全量人工审核,并明确平台法定审核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