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杀夫”女人辩护的30年

全球妇女峰会正在北京举行。
76岁的律师徐维华参加过30年前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一个让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实际上,在40多年前——那个“家暴”仍被视为“家务事”,更遑论女性主义与个体觉醒的年代,徐维华就已经扎进了中国女性权益最胶着也最复杂的现场。
媒体称她为“为杀夫女性辩护的人”。她代理的案件,构成了这30年间,女性在家庭暴力和土地权益中所遭遇困境的最真实切片。她曾经提到,“去村里维权的时候,有人说几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我想让他们看看,我们能掀起什么样的巨浪。”如今她告诉我们,自己越来越寄希望于年轻人,“新一代的女孩们总能在第一时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我们记录下她的故事。毕竟真正的改变,从来不只发生在会场上和宣言里,更发生在那些“于心不忍”的时刻,和一次次“掀起巨浪”的庭审中。
记者/高敏
编辑/雪梨王

庭审中,被告席上的李彦举起那只缺了一节中指的左手。
“你举着不要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断指是怎么回事。”辩护律师徐维华沉稳而坚定。法庭上原本的喧嚣随即陷入沉默。
这根手指,是被她的丈夫用菜刀砍下的。在经历了漫长的持续家暴后,她杀了丈夫,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而那截悬在空中的断指,成了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这一幕发生在2014年11月,成为徐维华三四十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刻度——从近乎无力,到终于能为一个陷入绝境的生命撬开一丝生存缝隙。
李彦被改判死缓,不久后,《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时间倒回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家庭暴力”概念的提出,给徐维华带来了冲击。彼时,她在全国妇联工作多年,参与起草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家暴”这个词,连同它揭示的被“家务事”外衣掩盖的性别暴力本质,成了她职业生涯的分野。
但现实总是无力。徐维华至今记得1998年代理的一个案子——一个河北女孩,在多次被丈夫当作赌资供人强奸后,拿起剪刀反抗,误杀了丈夫,被判死刑。徐维华为她奔走,电话打到了最高法,但最终也没能保住女孩的性命。
“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若干年后再提到这个案子,她的声音不自觉地抬高。这是她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也促使她提前退休离开体制,投入反家暴的民间战场。之后,我们看到了李彦案的转机,徐维华那句“你举着不要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断指是怎么回事”,不仅是律师的法庭策略,更是她凝聚了悲愤和经验的奋力一击。
如今76岁的徐维华仍固定每周去律所值班,接听求助者来电。她也会奔波在一线,为被剥夺土地的出嫁女、被提前退休的女性管理者和遭受职场性骚扰或精神控制的女性发声。
在家休息或出门遛弯时,她会听穿越、修仙、玄幻小说,自从做了白内障手术后,徐维华的这个习惯已经保留了十来年。耳机里是个快意恩仇的世界。听到公平正义被伸张,她觉得“很解气,特别爽”,似乎足以消解一部分现实中的无力。
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像小说里那样,穿越回去完成理想,但至少可以躬身入局,日拱一卒。
以下是徐维华的讲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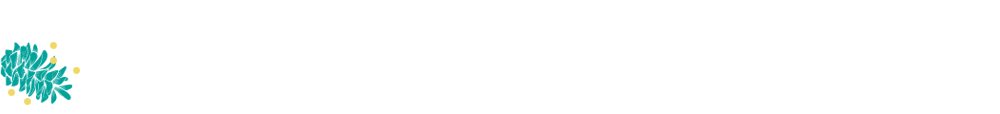
一次观念的冲击
我第一次听到“家庭暴力”这个说法,是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世妇会”)。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全国妇联工作。当时最关注的是妇女拐卖问题,我们还参与调研、起草和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这部法律在1991年出台,为中国争取承办世妇会打出了非常有利的一张牌。

徐维华在1995年世妇会上。
世妇会之前,我们花了半年时间去基层调研,也去高校、司法局、妇联收集意见。在论坛上,大家分享了中国当时在打击妇女儿童拐卖、遏制卖淫嫖娼、争取女性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益等各方面的成果和问题的讨论。
可是“家庭暴力”这个词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鲜的。
我第一次意识到,妇女在家庭中受到的虐待、残害甚至性侵,往往被“家庭”这种形式掩盖,被当作家务事。这是认知视角的缺失。家暴其实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应该从家庭范畴拎出来,也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当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并没有对家暴的定义,也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救助措施。在我们做权益工作的人眼里,妇女受到的伤害,不论是轻伤还是重度的残害,甚至被杀害,都属于人身权益范畴。当时大会上,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做了一场主题为“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的演讲。这个话在我们国家可能比较敏感,但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妇女儿童权利的保障,是一个国家对人身权益保障的尺度,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检验。对不对?

徐维华在世妇会第一次听到“家庭暴力”的说法。
受这场演讲的感召,我的校友郭建梅在世妇会后辞去了公职,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在民间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我当时觉得她离开体制内太可惜了。
我们俩是一起参与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战友”,当时组织给了我们很大权限去做调查研究,让放手去干。这部法律从没有到出台,花了五六年时间,立法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立法过程中,我和郭建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立下了共同的目标:保护妇女权益。虽然路径不同——她离开了单位,去民间帮助具体的个案;我在体制内,通过推动职能部门站在妇女立场保障她们的权益,但我们的理想是一致的。
“家庭暴力”概念的提出,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种观念的冲击。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被重视的问题。由于论坛的讨论时间有限,我们便主动去联系在反家暴领域经验更为丰富的专家,比如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同仁。通过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反对家庭暴力的支持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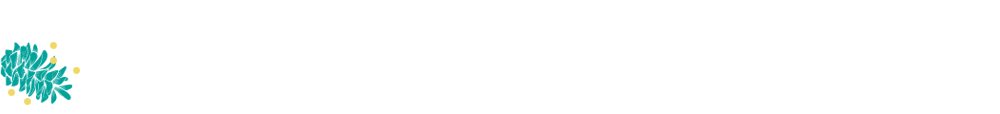
当然要救她
在这之后,妇联接手了很多家暴案例,反家暴也逐渐成了我工作的重心所在。这其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件,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将施暴的丈夫反杀。
1998年,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河北的一个案子,丈夫让人强暴妻子,后者杀夫。
男人是个富二代,很有钱,但是个赌徒。他赌博输了钱,就将妻子做了赌资,让赢钱的人去家里强奸自己的妻子。
当时他们新婚不久。第一次,女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没开灯,就发生了关系。她隐约觉得那人和丈夫不太一样,但也就睡了。第二次,也是黑着灯睡了。
等到第三次,女孩突然开了灯,一个陌生男人吓得翻到床下。他解释说,是经过她丈夫同意的。女孩觉得非常屈辱,为了自我保护,她买了一把剪刀塞到枕头下。结果第四次爬上床的是她的丈夫,当他在黑暗中试图与她发生关系时,女孩从枕下摸出剪刀捅了过去。
男人被割破动脉,死了。
这个案子一审判了故意杀人,死刑。女孩的家属向省高院上诉,也向妇联反映。我们当然要救她。她的丈夫实际上主使了对她的轮奸,这构成了与他人共同强奸妻子的犯罪,他不该死吗?女孩是强奸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卫,有什么不对?
接到女孩亲属寄给妇联的求助材料后,我们转给了河北省高院刑庭和最高法刑庭。我还打电话给最高法院刑庭,说明案子的特殊性,提出依法对女孩不判处死刑。接电话的庭长答应一定会慎重。但我去香港开会回来再去联系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女孩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事情我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法官手里握着的是人民赋予他的一把利剑,这把剑应该指向罪犯还是受害人?他们不懂吗?
这是我工作中一个非常失败的个例,也成了我心里的一个坎儿,始终过不去。如果将这个案件放到现在,我认为给她免罪处理都有可能。
2003年,我54岁那年选择了提前退休,与这件事也有一定关系。之后,我去了反家暴网络,这是一个试图从主流公检法机构、学术界以及社会宣传等多方面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暴力问题关注和行动的项目。
一年半后,我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代理反家暴案件。2012年,我正式加入了千千律师事务所,跟建梅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女性提供法律援助。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始终是我们职业最初的发心,我打内心里觉得,这也是我对自己职业的使命和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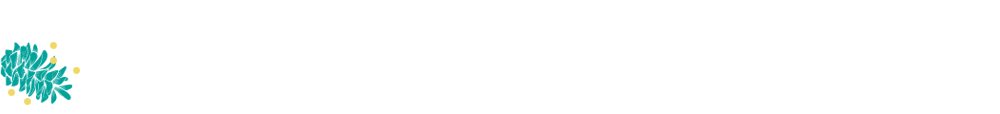
举起那根断指
在千千所,我们代理过一些“以暴制暴”反杀丈夫的个案。其中,李彦案是最让我感受到法治和时代进步的一起典型案例。
这个案子中,李彦和丈夫谭某都是再婚——李彦之前结过一次婚,谭某已经是第四次婚姻。据我们了解,他之前每次离婚都是因为家暴老婆。这次婚后没多久,谭某就开始打李彦,扇耳光,用烟头烫她,按住她的头往墙上撞,在她做完刮宫手术当晚还要强行发生关系。
李彦尝试过自救。她和家人一起,找派出所、社区和当地妇联求助,但事情被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没人帮她。她也提出过离婚,俩人拟了离婚协议,但因为谭某的车是李彦花钱买的,他没钱偿还,协议也就一直没签。
2010年的一个凌晨,谭某喝醉后,拿起气枪要打李彦。争执过程中,李彦拿起火药枪管砸向丈夫的后脑勺,后者被砸晕。李彦担心谭某醒来后对自己施暴,干脆将他砸死,之后分了尸,将尸块分装在塑料袋,沿隐蔽路段进行抛撒。
2011年,当地中级法院判李彦犯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二审也维持了原判。李彦的弟弟找到千千所求助,我和建梅决定一起为李彦辩护。
当时案子正处于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的阶段,也正好是《反家庭暴力法》酝酿期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包括媒体都在为李彦发声。2014年6月,案子的死刑复核没有通过,被发回二审法院重审。

徐维华在工作中。
2014年11月,二审重新开庭。在举证质证环节,我请求给李彦出示被家暴的受害部位证据的机会,审判长同意了。
我跟李彦说,请举起你的左手,给大家看看断指是怎么回事。
李彦左手中指缺了一个指节。她举着这只有断指的手,在法庭上陈述说,自己当时从朋友处得知谭某在外面与小三相会,就去了现场抓人。回家后,谭某问她,刚刚是用哪只手指着那个女人的,李彦说是左手。谭某继续追问,是哪根手指头,李彦伸出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谭某拿起菜刀砍了下去,“啪”地砍掉了一个指节。
在此之前,因为要面子,李彦对外都说是自己切肉时不小心砍断的。但这次面对的是生死问题,她陈述了事实。我记得我当时在庭上说,请大家以生活经验来判断,我们都做饭,切再大的骨头,都不会切到中指吧?谭某在婚姻中做了不忠的事情后,还对妻子进行暴力伤害,这多么残忍。李彦已经在努力自救了,但凡过得下去,她都不会做出杀人的事。可惜命运没有给她机会,但我们不能不救她。
当时庭上有很多男方的亲友,一直在用很难听的话骂我们。李彦把手指举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都没了。法庭的情况在这之后得到了扭转,我们也长舒了一口气。
李彦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首先跪向公婆,承认犯了罪,为自己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表达了忏悔;之后她面向法官,陈述自己因为家暴求助和投诉了好多次,也提出过离婚,但都没有机会保护自己,以至于酿成悲剧。她既是施害人,也是受害者。
我最后说,很遗憾以李彦的手杀了死者,但他(谭某)本人在整件事情中,也应该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在生死的紧要关头,一个女性要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能有什么办法?
2015年2月,李彦由死刑改判为死缓。之后,李彦还通过律师以自己的案件为例,向人大提出了修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建议。2015年12月27日,《反家庭暴力法》通过了,201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李彦,和她的家人也渐渐断了联系。2020年左右,她弟弟突然来电,告诉我李彦减刑了。只要她继续努力,多争取几次减刑,或许就能早一点儿重获自由。
这样的结果,在30年前,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争取不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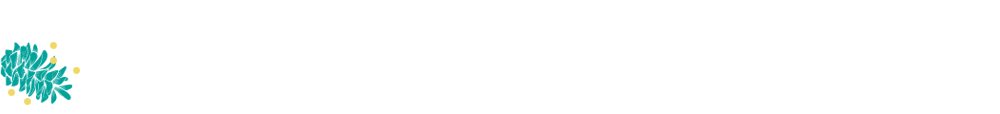
“我越来越寄希望于年轻人”
在我是1949年出生的。当时社会提倡的风气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从我出生、成长,到改革开放以前,“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接受度是很高的。
我刚参加工作,是在公安机关。过了半年的实习期后,大家不论男女,工资都一样,我拿36块,他们也是36块。在各方面的培训、提拔上,也都以个人表现作为依据。之后我去高校、妇联,乃至基层工作,单位领导给与了肯定,认为工作任务完成得比较有成效,也因此获得组织上的肯定。
在我所在环境中,或者说成长过程里,从来没有觉得男女有多大区别。
所以我也一直觉得女性跟男性享有同等权利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我大学学的是法律,在杭州大学任教期间,会作为法律顾问参与办理一些刑事案件。我参与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为一位女性被告人所做的辩护。她因为长期被人污蔑、侮辱、贬损,在忍无可忍、应激反应抑制不了的情况下,杀死了对方。
当时我单纯从法律角度出发,觉得这个女性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我作为她的辩护人,必须建立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证据为基础之上而提出的辩护。该案件最终没有轻判,但为作为被告人的妇女争得了生的希望。

徐维华在加拿大交流反家暴合作项目。
后来到了全国妇联,我一直秉持着这个朴素的观念,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就是我的工作。
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的过程中,我们去基层调研,才发现在“男女平等”口号之下,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事实,比如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在当时很猖狂,比如很多人有钱之后开始搞婚外情、婚内虐待、打骂老婆。由于那个年代倡导的生育政策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有的人为达到离婚再娶再生男孩的目的等种种情况,出现了不少换老婆的现象。社会治安方面也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等事件。
我认为当时出现的那些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情况。它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比如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提高女性参政的比例。这是为了提升女性的权利意识,旨在推动全社会对女性相关事务的重视关注,也促进女性的参与程度。
我们的理想当然是不断提高女性参政议政的比例,但这个比例现实中提高的速度比较缓慢,和我们期盼的还有差距。
从体制内出来后,我对女性权益问题有了更具体的感受。2010年前后,千千所接到了大量有关男女同龄退休问题的案件,同样处于管理岗位或者专业技术岗,依照法律规定,具有副处以上、副研究员以上职级、职称的人,可以享受60周岁退休的待遇。
但现实中女性被以各种理由在55岁退休的情况时有发生。毫无疑问,这就是男女不平等现象的突出表现。
这类案件我们当时接触了很多,但维权的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她们去提起行政诉讼,大部分屡诉屡败。我们还代理过一批浙江省退休女性的诉讼案件,最后也败诉了。
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以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中心的名义,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寄了材料,得到了他的重视。浙江省迅速专门派了人来北大汇报,给出了解决办法。
这是一个解决女性退休问题做得很好的特例,其他地方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也很难解决。
近些年,我们接到不少有关农村出嫁女土地权益的案子,这是农村已婚女性或者离婚女性面临的困境——村集体分给每户成员的宅基地,通常会分给家里的每个孩子,但村规民约认为,嫁出去的女性就是本村的外人,默认她们没有土地。而当出嫁女离婚、丧偶后,这个困境更加突出,她们早已失去了老家的土地,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以村民自治为名,不受制约地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也是国内目前基层治理中一种难以对抗的现象。现在想起来湖北一个村子的案例,我都觉得荒唐。
那个村里,很多出嫁女的土地被剥夺。她们层层往上反映问题,都难以解决。我们帮她们立了案,同时也找不少基层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本着这件事能在行政范围内解决是我们的愿望。我记得光是村委会主任,我们就找了好几趟。
那个村主任原本是个杀猪专业户,后来成为村委会主任。他在与我们的对话过程中说,他去找了省里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请教他们,都认为不能给出嫁女分配土地补偿费、集体经济分配款等款项,宅基地申请更得不到批准。我们与他反复说理、沟通。对方甚至说,你们向上反映、去投诉,我们可以组织村民公投,反正村里的男性成员跟出嫁女比起来,还是多数,(给她们征地补偿款、集体经济分配款等款项)是通不过的。
最终我们协商、协调未成。这类案子诉讼也大多都败诉,真的很荒唐。我始终觉得,虽然失去土地补偿款的出嫁女在农村属于少数,但她们的权益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她们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

徐维华仍然奔波于一线。
距离1995年世妇会过去30年了,国内妇女权益问题发展其实有不少进步的地方。比如大家不再担心“家丑不可外扬”,越来越多人清晰认识到家丑并不是你的原罪,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正因如此,我们接触到的以暴制暴的杀夫案也确实变少了。
随着法制教育的普及,大家都在学着对这种行为说“不”,这是女性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社会的进步。
当然,性别问题也在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近几年在舆论场比较突出的职场、高校性骚扰/性侵、看不见的精神暴力、精神控制等问题,我们也接到了许多求助。这些基于权力关系的侵害和暴力更隐形,更不易察觉,而且一旦造成伤害,很难取证。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推动,我们的政府部门、妇联和教育机构也应该更好地教会女性如何保护自己。
我倒是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90后”“00后”的年轻人认知觉悟越来越高,社会上发生的有关家庭暴力、虐待弱者的事件,新一代的女孩们总会在第一时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努力施以援手。
我越来越寄希望于这些年轻人。
我现在76岁了,只要我的思维能力还能适应,只要不被人反感,只要她们还需要,我就还会继续做。毕竟帮助她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下一篇:一抹志愿红 共绘幸福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