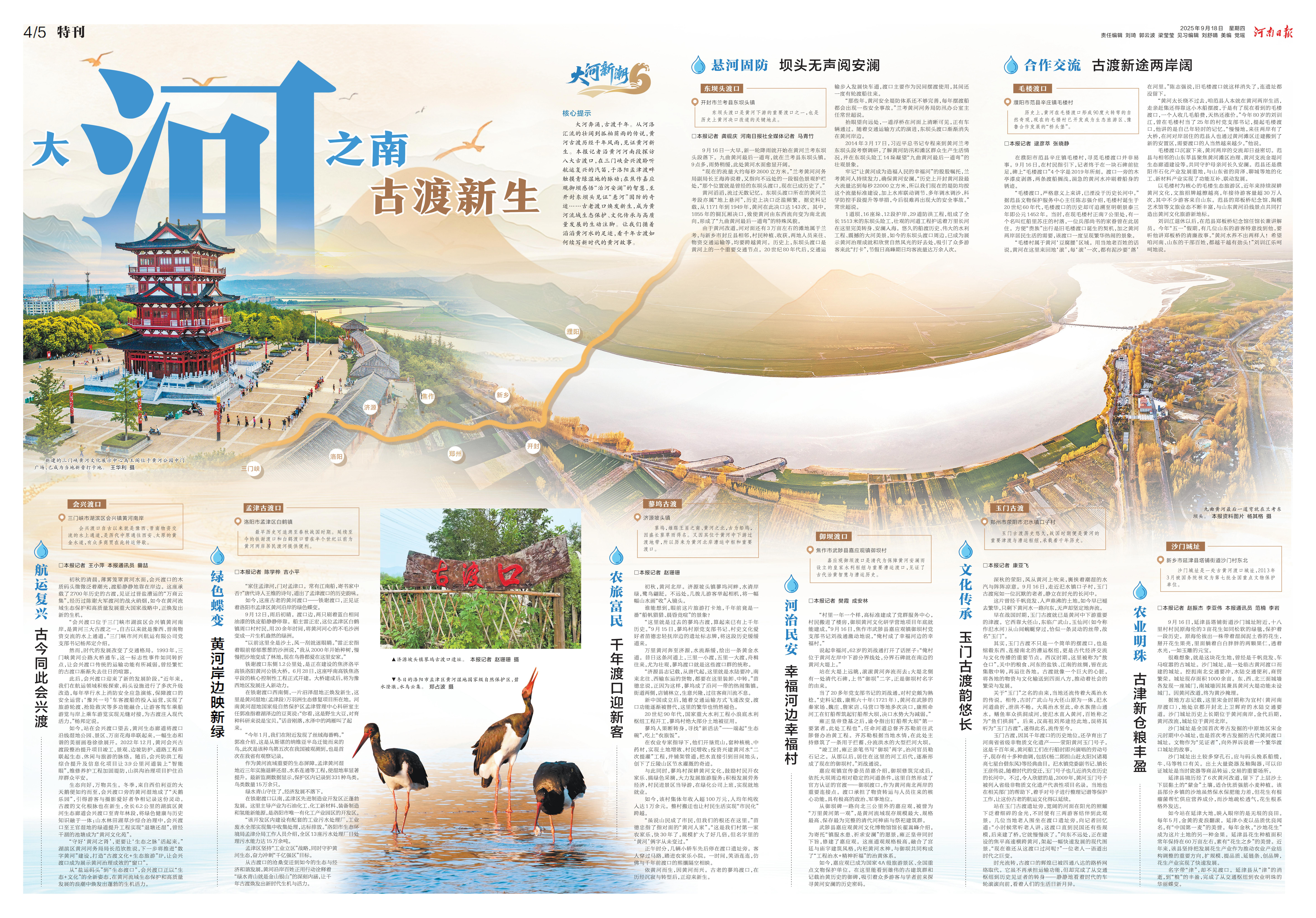大河新潮丨大河之南 古渡新生
核心提示
大河奔涌,古渡千年。从河洛汇流的壮阔到孤柏荫雨的传说,黄河古渡历经千年风雨,见证黄河新生。本报记者沿黄河河南段探访八大古渡口,在三门峡会兴渡聆听航运复兴的汽笛,于洛阳孟津渡畔触摸青绿湿地的脉动;在焦作嘉应观御坝感悟“治河安澜”的智慧,至开封东坝头见证“悬河”固防的奇迹……古老渡口焕发新生,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让我们循着滔滔黄河水的足迹,看千年古渡如何续写新时代的黄河故事。
悬河固防 坝头无声阅安澜

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就在兰考东坝头。 河南日报资料图片 杨其格 摄
东坝头渡口
开封市兰考县东坝头镇
东坝头渡口是黄河下游的重要渡口之一,也是历史上黄河决口改道的关键地点。
9月16日一大早,新一轮降雨就开始在黄河兰考东坝头段落下。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就在兰考县东坝头镇。9点多,雨势稍缓,此处黄河水面愈显开阔。
“现在的流量大约每秒2600立方米。”兰考黄河河务局副局长王海涛说着,又指向不远处的一段银色景观护栏处,“那个位置就是曾经的东坝头渡口,现在已成历史了。”
黄河滔滔,流过无数记忆。东坝头渡口所在的黄河兰考段亦属“地上悬河”,历史上决口泛滥频繁。据史料记载,从1171年到1949年,黄河在此决口达143次。其中,1855年的铜瓦厢决口,致使黄河由东西流向变为南北流向,形成了“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特殊风貌。
由于黄河改道,河对面还有3万亩左右的滩地属于兰考,与新乡市封丘县相邻,村民种植、收获,两地人员来往、物资交通运输等,均要跨越黄河。历史上,东坝头渡口是黄河上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20世纪80年代后,交通运输步入发展快车道,渡口主要作为民间摆渡使用,其间还一度有轮渡船往来。
“那些年,黄河安全堤防体系还不够完善,每年摆渡船都会出现一些安全事故。”兰考黄河河务局防汛办公室主任常世超说。
抬眼望向远处,一道浮桥在河面上清晰可见,正有车辆通过。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演进,东坝头渡口渐渐消失在黄河岸边。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黄河兰考东坝头段考察调研,了解黄河防汛和滩区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并在东坝头险工14垛凝望“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壮观景象。
牢记“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殷殷嘱托,兰考黄河人持续发力,确保黄河安澜。“历史上开封黄河段最大流量达到每秒22000立方米,所以我们现在的堤防均按这个流量标准建设,加上水库联动调节、多年调水调沙、科学防控手段提升等举措,今后很难再出现大的安全事故。”常世超说。
1道坝、16座垛、12段护岸、29道防洪工程,组成了全长1513米的东坝头险工,壮观的河道工程护送着万里长河在这里完美转身、安澜入海。悠久的船渡历史、伟大的水利工程、震撼的大河美景,如今的东坝头渡口周边,已成为展示黄河治理成就和欣赏自然风光的好去处,吸引了众多游客来此“打卡”,节假日高峰期日均客流量达万余人次。(河南日报记者 龚砚庆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青竹)
合作交流 古渡新途两岸阔
毛楼渡口
濮阳市范县辛庄镇毛楼村
历史上,黄河在毛楼渡口形成90度大转弯的自然奇观,现在的毛楼村已开发成为生态旅游区、豫鲁合作发展的“桥头堡”。
在濮阳市范县辛庄镇毛楼村,寻觅毛楼渡口并非易事。9月16日,在村民指引下,记者终于在一块石碑前驻足,碑上“毛楼渡口”4个字是2019年所刻。渡口一旁的木亭漆皮剥落,两条渡船搁浅,湍急的黄河水冲刷着船身的锈迹。
“毛楼渡口,严格意义上来讲,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据范县文物保护服务中心主任陈志强介绍,毛楼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毛楼渡口的历史却可追溯至明朝景泰三年即公元1452年。当时,在现毛楼村正南7公里处,有一个名叫红船里苏庄的村落,一位兵部尚书的家眷曾在此居住。方便“贵族”出行是旧毛楼渡口诞生的契机,加之黄河两岸居民生活的需要,该渡口一度呈现繁华热闹的景象。
“毛楼村属于黄河‘豆腐腰’区域。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黄河在这里来回地‘滚’,每‘滚’一次,都有泥沙要‘落’在河里。”陈志强说,旧毛楼渡口就这样消失了,连遗址都没留下。
“黄河太长绕不过去,咱范县人本就在黄河两岸生活,走亲赶集还得靠这小木船摆渡,于是有了现在看到的毛楼渡口,一个人收几毛船费,天热还涨价。”今年80岁的刘训江,曾在毛楼村当了2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提起毛楼渡口,他讲的是自己年轻时的记忆。“慢慢地,来往两岸有了大桥,在河对岸居住的范县人也通过黄河滩区迁建搬到了新的安置区,需要渡口的人当然越来越少。”他说。
毛楼渡口沉寂下来,黄河两岸的交流却日益密切。范县与相邻的山东莘县聚焦黄河滩区治理、黄河支流金堤河生态廊道建设等,共同守护母亲河长久安澜。范县还是濮阳市石化产业发展重地,与山东省的菏泽、聊城等地的化工、新材料产业实现了功能互补、联动发展。
以毛楼村为核心的毛楼生态旅游区,近年来持续深耕黄河文化,文旅招牌越擦越亮,年接待游客量超30万人次,其中不少游客来自山东。范县的郑板桥纪念馆、陶模艺术馆等文旅业态不断丰富,与山东黄河沿线景点共同打造出黄河文化旅游新地标。
刘训江退休以后,在范县郑板桥纪念馆任馆长兼讲解员。今年“五一”假期,有几位山东的游客特意找到他,要听他讲郑板桥的清廉故事。“黄河水养不出两样人!希望咱河南、山东的干部百姓,都越干越有劲头!”刘训江乐呵呵地说。(河南日报记者 逯彦萃 张晓静)
航运复兴 古今同此会兴渡

新建的三门峡黄河文化展示中心禹王阁位于黄河公园中门广场,已成为当地新晋打卡地。 王华利 摄
会兴渡口
三门峡市湖滨区会兴镇黄河南岸
会兴渡口自古以来就是豫西、晋南物资交流的水上通道,是历代中原通往西安、太原的黄金水道,有众多商贾在此转运停歇。
初秋的清晨,薄雾笼罩黄河水面,会兴渡口的木质码头微微泛着潮光,渡船静静地靠在岸边。这座承载了2700年历史的古渡,见证过晋盐漕运的“万商云集”,经历过陈谢大军渡河的战火硝烟,如今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中,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会兴渡口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会兴镇黄河南岸,是黄河三大古渡之一,自古以来就是豫西、晋南物资交流的水上通道。”三门峡市河兴航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杨邦定介绍。
然而,时代的发展改变了交通格局。1993年,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通车,这一标志性事件如同转折点,让会兴渡口传统的运输功能有所减弱,曾经繁忙的古渡口渐渐失去往日的喧嚣。
此后,会兴渡口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我们在航运领域积极探索,码头设施进行了多次升级改造,每年举行水上消防安全应急演练,保障渡口的安全运营;‘豫兴一号’车客渡船的投入运营,实现了旅游轮渡、抢险救灾等多功能融合,让游客驾车乘船游览与岸上乘车游览实现无缝对接,为古渡注入现代活力。”杨邦定说。
如今,站在会兴渡口望去,黄河生态廊道将渡口沿线湿地公园、景区、万亩花海串联起来,一幅生态和谐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2022年12月,黄河会兴古渡段整治提升项目竣工,景观、边坡防护、道路工程串联起生态、休闲与旅游的脉络。随后,会兴防洪工程综合提升及信息化项目让3.9公里河道装上“智能眼”,维修养护工程加固堤防,山洪沟治理项目护住沿岸群众平安。
生态向好,万物共生。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大天鹅便如约而至,会兴渡口旁的黄河湿地成了“天鹅乐园”,引得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争相记录这份灵动。古渡的文化根脉也在新生,全长6.2公里的湖滨区黄河生态廊道会兴渡口至青年林段,将绿色健康与历史知识融于一体;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中,会兴渡口至王官湿地的绿道提升工程实现“退塘还湿”,曾经干涸的池塘成为“黄河文化苑”。
“守好‘黄河之肾’,更要让‘生态之脉’活起来。”湖滨区黄河河务局局长范钦胜说,下一步将推进“数字黄河”建设,打造“古渡文化+生态旅游”IP,让会兴渡口成为展示黄河治理成效的“窗口”。
从“盐运码头”到“生态渡口”,会兴渡口正以“生态+文化”的全新姿态,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活力。(河南日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日报通讯员 爨喆)
绿色蝶变 黄河岸边映新绿

冬日的洛阳市孟津区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碧水澄澈,水鸟云集。 郑占波 摄
孟津古渡口
洛阳市孟津区白鹤镇
最早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延续至今的铁谢渡口和白鹤渡口曾在半个世纪以前为黄河两岸居民渡河提供便利。
“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道出了孟津渡口的历史韵味。
如今,这座古老的黄河渡口——铁谢渡口,正见证着洛阳市孟津区黄河沿岸的绿色蝶变。
9月12日,雨后初晴。渡口边,两只刷着蓝白相间油漆的铁皮船静静停靠。船主雷正宏,这位孟津区白鹤镇周口村村民,用20余年时间,将黄河河心的不毛沙洲变成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
“以前这里全是沙土,风一刮就迷眼睛。”雷正宏指着眼前郁郁葱葱的沙洲说,“我从2000年开始种树,慢慢把沙地变成了林地,现在鸟兽都爱在这里安家。”
铁谢渡口东侧1.2公里处,是正在建设的焦济洛平高铁洛阳黄河公铁大桥。6月28日,这座呼南高铁焦洛平段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正式开建。大桥建成后,将为豫西地区发展注入新动力。
在铁谢渡口西南侧,一片沼泽湿地正焕发新生,这里是黄河湿地(孟津段)万羽洲生态修复项目所在地。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指着湖泽边的豆荚说:“你看,这是野生大豆,对育种科研来说是宝贝。”话音刚落,水泽中的鸿雁叫了起来。
“今年1月,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丝绒海番鸭。”郭准介绍,这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而来的鸟,此次是该种鸟第五次在我国被观测到,也是首次在我省有观察记录。
作为黄河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孟津黄河湿地近三年实施退耕还湿、水系连通等工程,使湿地率显著提升。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保护区内记录到331种鸟类,鸟类数量15万余只。
绿水青山守住了,经济发展不落下。
在铁谢渡口以南,孟津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正蓬勃发展。这里主导产业为石油化工、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和氢能新能源,是洛阳市唯一有化工产业园区的开发区。
“该开发区内建设有配套的工业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全部实现集中收集处理,达标排放。”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孟津分局工作人员介绍,全区13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能力达15万余吨。
孟津区坚持“工业立区”战略,同时守护黄河生态,奋力冲刺“千亿强区”目标。
从古渡口的沧桑变迁到如今的生态与经济和谐发展,黄河沿岸百姓正用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让千年古渡焕发出新时代生机与活力。(河南日报记者 陈学桦 吉小平)
农旅富民 千年渡口迎新客

济源坡头镇蓼坞古渡口遗址。 河南日报记者 赵珊珊 摄
蓼坞古渡
济源坡头镇
蓼坞,雄踞王屋之南、黄河之北,古为船坞,因盛长蓼草而得名。又因其位于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所以历来为黄河北岸漕运中枢和重要渡口。
初秋,黄河北岸。济源坡头镇蓼坞河畔,水清岸绿,鹭鸟翩跹。不远处,几拨儿游客举起相机,将一幅幅山水画“收”入镜头。
谁能想到,眼前这片旅游打卡地,千年前竟是一番“船帆猎猎、晨昏竞喧”的景象?
“这里就是过去的蓼坞古渡,算起来已有上千年历史。”9月15日,蓼坞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史文化爱好者苗德忠轻抚岸边的遗址标志牌,将这段历史缓缓道来。
万里黄河奔至济源,水流渐缓,绘出一条黄金水道。昔日这条河道上,三里一小渡,五里一大渡,舟楫往来,尤为壮观,蓼坞渡口就是这些渡口群的统称。
“济源县志记载,从唐代起,这里就是水陆要冲,南来北往、西输东运的货物,都要在这里装卸、中转。”苗德忠说,正因为这样,蓼坞成了沿河一带的热闹集镇。街道两侧,店铺林立,生意兴隆,过往客商川流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交通运输方式飞速改变,渡口功能逐渐被替代,这里的繁华也悄然褪色。
20世纪90年代,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开工,蓼坞村绝大部分土地被征用。
蓼坞人果断转身,寻找“新活法”——端起“生态碗”,吃上“农旅饭”。
在农业专家指导下,他们开垦荒山,套种核桃、中药材,实现土地增效、村民增收;投资兴建黄河水“二次提灌”工程,并铺架管道,把水直接引到田间地头,创下了丘陵山区节水灌溉的奇迹。
与此同时,蓼坞村深耕黄河文化,鼓励村民开农家乐、搞绿色采摘,大力发展旅游服务;积极发展劳务经济,村民进景区当导游,在绿化公司上班,实现就地就业。
如今,该村集体年收入超100万元,人均年纯收入达1万余元。整村搬迁也让村民生活实现“市民化”跨越。
“虽说山民成了市民,但我们的根还在这里。”苗德忠指了指对面的“黄河人家”,“这是我们村第一家农家乐,快30年了,规模扩大了好几倍,但名字里的‘黄河’俩字从未变过。”
正午时分,几辆小轿车先后停在渡口遗址旁。客人穿过马路,踏进农家乐小院。一时间,笑语连连,仿佛与千年前渡口的熙攘隔空相映。
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古老的蓼坞渡口,在历经沉寂与转型后,正迎来新生。(河南日报记者 赵珊珊)
河治民安 幸福河边幸福村
御坝渡口
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镇御坝村
嘉应观御坝渡口是清代为保障黄河安澜而设立的皇家水利枢纽与重要漕运渡口,见证了古代治黄智慧与漕运历史。
“村里一年一个样,高标准建成了党群服务中心,村民搬进了楼房,御坝黄河文化研学营地项目年底就能建成。”9月16日,焦作市武陟县嘉应观镇御坝村党支部书记刘战通激动地说,“俺村成了幸福河边的幸福村。”
说起幸福河,62岁的刘战通打开了话匣子:“俺村位于黄河左岸中下游分界线处,分界石碑就在南边的黄河大堤上。”
站在大堤上远眺,滚滚黄河奔流而去;大堤北侧有一处清代石碑,上书“御坝”二字,正是御坝村名字的由来。
当了20多年党支部书记的刘战通,对村史颇为熟稔。“史料记载,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在武陟的秦家场、魏庄、詹家店、马营口等地多次决口,康熙命河工在钉船帮筑起钉船帮大坝,决口水势大为减弱。”
雍正皇帝登基之后,谕令指出钉船帮大坝“第一要紧者,此处工程也”,任命河道总督齐苏勒前往武陟督办治黄工程。齐苏勒根据当地水情,在此处主持修筑了一条用于拦蓄、分流洪水的大型拦河大坝。
“竣工时,雍正亲笔书写‘御坝’两字,治河官员勒石记之。从那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河工后代,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御坝村。”刘战通说。
嘉应观镇宣传委员苗嘉介绍,御坝修筑完成后,依托大坝周边相对稳定的河道条件,这里自然形成了官方认证的官渡——御坝渡口,作为黄河南北两岸的重要连接点。渡口承担了物资转运与人员往来的核心功能,具有极高的政治、军事地位。
从御坝碑一路向北三公里外的嘉应观,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观”,是黄河流域现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河神庙与祭祀建筑群。
武陟县嘉应观黄河文化博物馆馆长翟嵩峰介绍,为寄托“镇服水患、祈求安澜”的愿景,雍正皇帝同时下旨,修建了嘉应观。这座道观规格极高,融合了宫廷与庙宇建筑风格,内祀黄河水神,与御坝共同构成了“工程治水+精神祈福”的治黄体系。
如今,嘉应观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能看到雄伟的古建筑群和记载治黄历史的御碑,吸引着众多游客与学者前来探寻黄河安澜的历史密码。(河南日报记者 樊霞 成安林)
文化传承 玉门古渡韵悠长
玉门古渡
郑州市荥阳市汜水镇口子村
玉门古渡历史悠久,战国时期便是黄河的重要津渡与漕运枢纽,承载着千年历史。
深秋的荥阳,风从黄河上吹来,裹挟着潮湿的水汽与阵阵凉意。9月16日,走近汜水镇口子村,玉门古渡宛如一位沉默的老者,静立在时光的长河中。
这片曾经千帆竞发、人声鼎沸的土地,如今早已褪去繁华,只剩下黄河水一路向东,无声却坚定地奔流。
早在战国时期,玉门古渡就已是黄河中下游重要的津渡。它西靠大伾山,东临广武山,玉仙河(如今称作汜水河)从山间蜿蜒穿过,恰似一条灵动的丝带,故名“玉门”。
其实,玉门古渡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摆渡口,也是绾毂东西、连接南北的漕运枢纽,更是古代经济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节点。西汉时期,这里被称为“敖仓口”,关中的粮食、河东的盐铁、江南的丝绸,皆在此集散中转,再运往各地。古渡就像一个巨大的心脏,将各地的物资与文化输送到四面八方,推动着社会的繁荣与发展。
关于“玉门”之名的由来,当地还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相传,古时广武山与大伾山原为一体,汜水河道曲折,泄洪不畅。大禹治水至此,命水族凿山通水。鳝鱼率众拱洞成河,使汜水直入黄河,百姓称之为“鱼们拱洞”。后来,汉高祖刘邦途经此地,误将其听为“玉门古渡”,遂得此名,流传至今。
玉门古渡,因其千年渡口的历史地位,还孕育出了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荥阳黄河玉门号子。这是千百年来,黄河船工们在行船时即兴演唱的劳动号子,现存有十多种曲调,包括《杨二郎担山赶太阳》《诸葛亮七星台借东风》等经典曲目。汜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彦伟说,随着时代的变迁,玉门号子也几近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令人欣慰的是,2009年,黄河玉门号子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地也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着手对号子进行整理记谱等保护工作,让这份古老的航运文化得以延续。
站在玉门古渡遗址旁,宽阔的河面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细碎的金光,不时便有三两游客结伴到此观景。几位当地老人围坐在渡口遗址旁,向记者回忆道:“小时候常听老人讲,这渡口直到民国还有些规模,后来建了桥,它就慢慢淡了。”向东不远处,正在建设的焦平高速横跨黄河,架起一幅快速发展的现代图景。“现在谁还从这渡口过河呢?”一位老人一语道出时代之巨变。
时光流转,古渡口的辉煌已被四通八达的路桥网络取代。它虽不再承担运输功能,但却完成了从交通枢纽到历史见证者的转身——静静地看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看着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河南日报记者 康亚飞)
农业明珠 古津新仓粮丰盈
沙门城址
新乡市延津县塔铺街道沙门村东北
沙门城址是一处古黄河渡口城址,2013年3月被国务院核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月16日,延津县塔铺街道沙门城址附近,十八里村村民原海伦的3亩花生如同松软的绿毯,保护着一段历史。原海伦拔出一株带着湿润泥土香的花生,掰开花生果壳,里面躺着白白胖胖的两颗果仁,透着水光,一如玉雕的元宝。
很难想象,就是这块花生地,曾经是千帆竞发、车马喧嚣的古城址。沙门城址,是一处临古黄河渡口而建的城址。控扼南北交通要冲,水陆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城址现存面积1000余亩。东、西、北三面城墙各发现一座城门,南城墙因其兼具黄河大堤功能未设城门。因黄河改道,终为黄沙掩埋。
据地方志记载,这里宋金时期称为宜村(黄河南岸渡口),地处京都开封北上卫辉府的水陆交通要道。沙门城址历史上长期位于黄河南岸,金代后期,黄河改流,城址位于黄河北岸。
沙门城址是全国首次考古发掘的中原地区宋金元时期中小城址,也是首次考古发掘的古代黄河渡口城址。文物作为“见证者”,向外界诉说着一个繁华渡口城址的故事。
沙门城址出土较多穿孔石,应与码头挽系船缆,牛、马等牲口有关。出土大量瓷器及釉陶器,可以印证城址是当时瓷器等商品转运、交易的重要场所。
延津县境历经了6次黄河改道,留下了上层沙土下层黏土的“蒙金”土壤,适合优质强筋小麦种植。该县部分乡镇的沙地虽然保水保肥能力差,但花生有根瘤菌帮忙供应营养成分,而沙地疏松透气,花生根系格外发达。
如今站在延津大地,映入眼帘的是无垠的良田。每年5月,金黄的麦浪翻滚。延津小麦以品质优良闻名,有“中国第一麦”的美誉。每年金秋,“沙地花生”成为这片土地的另一种金果。延津县花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60万亩左右,素有“花生之乡”的美誉。近年来,该县坚持把发展花生产业作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扩规模、提品质、延链条、创品牌,花生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
名字带“津”,却不见渡口。延津县从“津”的消逝,到“粮”的丰盈,完成了从交通枢纽到农业明珠的华丽蝶变。(河南日报记者 赵振杰 李亚伟 河南日报通讯员 范楠 李岩)